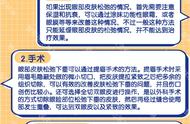大部分美洲野牛个体通体呈咖啡色,但有时也会出现部分出生时全身覆盖白色毛发的野牛。通常情况下,这并非由白化病所致,因为这些个体的身体,如皮肤,毛发和眼睛仍然会整正常生产颜料色素,并在渐渐长大后变回啡色。但有些则是白化症,即使长大了也是白色。白野牛更被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认为是神圣的动物。美洲野牛的交配习性为一夫多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分为离群公牛与带仔母牛群两类族群各自生活,只有夏季中后部分的繁殖季节才会聚集在一起。单身的雄性公牛会在交配完成之前一直“看管”雌性野牛群,期间会与附近前来竞争的其他雄性发生争斗。年幼的美洲野牛毛色会比成年野牛稍浅。不过在游戏中,异色爆炸头水牛的毛色为酒红色,牛角的颜色要比正常配色略泛红光,爆炸头的颜色也更深。白野牛则并未有原型上的体现。


从物种迁徙的角度看,美洲野牛并非北美洲的原生物种。与亚洲水牛一样,它们源自欧亚大陆,后来通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大约在距今10,000年前,美洲野牛取代了当时数量庞大的西伯利亚野牛——另一种来自欧亚大陆的野牛移居种类。在此期间,虽然遭到野狼以及人类狩猎,但美洲野牛仍然以极强的适应性成为了北美洲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基石物种。到了公元14世纪,生活在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达到了3000万到6000万左右。

讽刺的是,因移民美洲而走向繁荣的美洲野牛,却同样因为另一个移民美洲的物种——欧洲殖民者而遭受了灭顶之灾。时间来到19世纪,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后,出于大量商业化获取牛皮,以及减少印第安人食物来源等目的,对美洲野牛进行了大量屠*。19世纪70年代,德国发明了一种将野牛皮鞣制成细皮革的工艺。这使得美洲野牛皮的应用更加宽广,需求量大大提升,也最终让这一可怜的大型物种逼上了绝路。到了1884年,美国境内只剩下325头野生野牛,其中25只被保护在黄石公园。这已不及14世纪美洲野牛种群最低估计数量的十万分之一。万幸的是,工业化的车轮最终放过了这些北美洲特有的野牛,在百余年的严格保护下,如今美国境内的野生美洲野牛种群数量恢复到了1万头左右;其中黄石公园境内的种群恢复到了4900头左右,是数量最多的纯种野牛群。然而,若非人类的滥捕滥*,又怎会有美洲野牛曾经万不余一的惨剧?而这样的惨剧,如今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