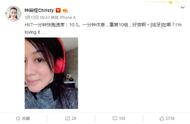牛化东(1906-1995)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用名牛杰,牛殿英。陕西定边王来滩村人。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1927年被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在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团长。1945年10月25日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一、定边高小入党
我是陕西省定边县王来滩人。1925年8月在定边高等小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党。据我所知,当时定边党员有汤仲甫、赵炳日、龙惠民、丁子齐、郭子范、马兰等;安边党员有刘世庵、冯子舟、李锦春、刘子贞、田佐勤、吕振华、沈玉娥(女)等。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绥德四师、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毕业后都陆续回到本地搞地下工作。同时,从外地来的党员有周梦雄、周发源。以上这些人是定边最早期的党员,是定边党组织的“创始人”。
那时,地下党员大多数分布在教育界,主要任务是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我曾记得,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地下党员,工作很认真。他们除教授学生学好国文、算术、史地、体育等文化课外,还经常给学生发一些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让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经过他们的精心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眼界开阔了,思想进步了。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收入党的。
1926年放暑假的一天,汤仲甫、周梦雄、丁子齐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并通知我到城南沙窝宣誓。宣誓地点是在一个四周高、中间凹的沙丘里进行的。为了保密起见,还派一个人在沙梁上放哨。参加我人党宣誓仪式的还有赵炳日、龙惠民、周发源等人。我记得当时介绍人讲了话,我宣了誓,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我们分散回到城内。我就是定边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人了。此后有张元桢、黄明(又叫黄庚甫),还有一个榆林毛毛匠的儿子叫要希贤的先后也人了党。
二、领导闹学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们定边的地下党员在“五四”运动革命精神鼓舞下,于1926年前后,组织和领导学生闹学潮,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改组“劝学所”,夺回教育权。当时定边的教育权(包括教育经费、房屋、土地等)掌握在当地绅士所控制的“劝学所”一些人手里,有些绅士就是“动学所”所长。他们向学生灌输旧封建礼教,束缚学生思想的发展,对我们开展活动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就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向绅士展开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孤立顽固派,争取和团结进步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
佘鼎九是定边有名望的绅士,是定边文武二“圣人”的“武圣人”。他既是“劝学所”所长,又带民团;既掌握着兵权,又有教育权,但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绅上。所以,我们就积极做他的工作,争取他的支持,以便达到把“动学所”改组为教育局,把绅士所管的教产收归教育局,用教育经费办平民职业学校等目的。当时,绅士白炳汉是顽固派,他勾结国民党定边县县长丁鸿藻,不愿意把教产交出来。但佘鼎九支持我们,他说:“你们出头,我说话”。当时县长对佘鼎九也有些怕,我们就利用这些矛盾,积极进行斗争。在我们的斗争和佘鼎九支持的影响下,贾新庄贾仁、郑尔庄张怀明等绅士也支持我们收回教产的斗争。这样一来,使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女得到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在乡下念私塾,没钱进“洋学堂”的状况。我们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教育局也成立了,共产党员汤仲甫当了教育局长,教产也收回来了。
与此同时,学校也更换了一些教员,我曾记得,当时教育局把定边的苗举人和姓李的校长(关中人)等前清秀才都换掉了。聘请郝秀升、段景文、栾本植和一个姓施的(名字记不清了)当了教员。这些人的到来,再加上原有的地下党员教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二)成立“天足会”,惹怒县太爷。那时定边的妇女和全国一样,都时兴缠脚。缠脚对妇女摧残的很厉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解除妇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定边高小为主,专门成立了“天足会”。郭子范任会长,我是副会长。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天足会”的工作阻力很大。为了打开局面,我们研究确定先从两个有名气的人身上“开刀”。一个是县长丁鸿藻的小老婆,一个是绅士百病汉的小老婆。丁县长的小老婆是定边东街冯皮匠的女儿,还没有娶过门,头也上了,就准备马上成亲,我们“天足会”的学生就到冯皮匠家里动员他女儿放脚。冯皮匠依仗县长的权势,顽固不化,三言两语就和我们吵了起来,并煽动皮房工人和我们打架。由于人家人多势众,最后把我们赶跑了。第二天,我们动员全校师生一起出动,到冯皮匠家里,把县长小老婆的绣花鞋,裹脚布都脱了,把冯皮匠搞得很狼狈。到县长正式成亲的那天,我们又赶去,把酒席砸了。这一下闯下了大乱子,惹怒了县长,他派人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局长是何其智,副局长王聚英。后来我到宁夏做军运工作时才知道王聚英也是地下党员,难怪当时把我们抓去以后,王对我们很热情,又是给我们弄饭吃,又是给我们宽心开导,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被县长关起来后,学校的地下党员,为营救我们,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再加上佘鼎九出面调解,丁县长见势不妙,只好答应放我们出去,并表示今后再不干涉我们“天足会”的工作。
那时,杨虎城部驻定边,有一个齐营长很坏,这家伙与丁鸿藻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经常干预学生运动,和学生关系闹得很对立,很紧张,有时竟以武力威胁我们。佘鼎九当时支持学生,情况一紧张,他就睡在学校,同时还给学生发了几十支驳壳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们有佘鼎九的支持,胆子更大了,腰杆子更硬了,就跟齐营长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结果,齐营长收敛了,从此再也不干涉学生的行动了。
(三)反对天主教,把洋人驱逐出定边城。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进行文化渗透。所以,外国洋人到处修建教堂。当时,洋人除在定边县白泥井、堆子梁一带修建了教堂外,还想在定边城内和城附近修建教堂,欺骗、毒害人民。我们就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在街南游说,我们就在街北讲演。我们主要揭露洋人的罪恶目的和他们的欺骗宣传,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当时闹得很凶,洋人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唱对台戏,当面痛斥。汤仲甫嫌学生讲得不带劲,就亲自登台讲演。汤的气魄大,讲得好,弄得洋人没有一点办法,最后,终于被我们轰出了城。所以,定边城以及城附近始终没有修起一个教堂。定边“眼光庙”里有个“同善社”,是个迷信组织。有一天,我们有几个学生冲进庙里,三锤两棒子就把“同善社”给捣毁了。
我们的这些行动,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拍手称快。但丁鸿藻却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报复。正当学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丁鸿藻又把几个学生抓了起来,罗织罪名,说我们砸“同善社”是犯上作乱,亵渎神灵。但我们不理睬他那一套,继续进行说理斗争。丁见我们态度强硬,加上佘鼎九又出来为我们说话了。他对丁鸿藻说:“学生娃娃嘛!你们不能那样,动不动就抓起来,快放了。”佘鼎九说话丁县长也不敢不听,只好把学生放了。
三、兰州监狱的斗争
1926年我在定边高小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推荐到冯玉祥在兰州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全称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这次来陕北招收学生的是个江西人,名叫钱清泉(地下党员),少将军衔,是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当时,被招收的学生有的是党员,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的;有的是非党群众,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去的,成分比较复杂。我们一起离开定边先到宁夏。到宁夏以后,就把陶新亚、李临民、郭维化等地下党员留下了,以后他们就搞起了个宁夏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由地下党领导的。三边到兰州的还有石英秀介绍的孙志元、党君祥等人。和我们一块到兰州的地下党员只有我和丁广智、吕振华三个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对共产党实行血腥镇压。到1928年,国民党还继续搞“清党”运动,三天两头抓人,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兰州军校也不例外。但由于冯玉祥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许多共产党员被抓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不晓得。先是钱清泉不见了,随后,地下党员、学校政治部主任王孝锡(清华大学学生)也不见了。我们还议论说:“孝锡哪儿去了!”接着地下党员马林山、胡清祯、贾宗周等人都不见了。后来,我和一个地下党员马尔逊(清华大学学生)被抓进了监狱,才真相大白了。原来国共两党分裂了,蒋介石搞“清党”运动。
我们被抓进监狱,有两条所谓罪状:一是钱清泉招收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二是发现王孝锡一个小本子上记了许多人的名字,怀疑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是王孝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时记下的名单,哪能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是地下党员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连冯玉祥部队里军长、师长的儿子也抓进来了。宋子元不是共产党员也被抓进来了。我们被抓进监狱,反倒比在外面知道的消息多。敌人也知道谁是共产党的主要人,谁是一般党员。所以,把我和马尔逊都单独关押,也有两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那都是普通党员。听说王孝锡在狱中斗争得很坚决,敌人严刑拷打,他什么也不招认。当时是冬天,我们就在炕席下边用火钳子钻了小洞,纸条进行联系,坚持斗争。当时,冯玉祥部队军长、师长的儿子也进行反抗,他们的家属闹得更凶。敌人看这样闹下去也不好,没有抓到真正把柄,所以就把抓进去的人编成“三民主义教育班”,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锥力学给我们讲课。学习了两个月,还进行了考试。当时地下党员都考得好,最后就把我们分配了。人家军长、师长的儿子仍回学校,地下党员被分到陕西的、甘肃的到处都有,我当时被分到甘肃无线电传习所当管理员,负责上街买材料修房子。有一天,在街上碰见吕振华,互相商量,仍回三边找党组织。但吕还在学校,行动不十分自由,我在“传习所”比较自由,所以商定谁得便,谁就走。后来,我就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机会,偷偷跑到黄河边雇了一个木筏子,顺水一下子流到宁夏吴忠。1928年四五月间,我又回到了定边,在定边高小任体育课教员。但学校党组织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和过组织生活,无疑是审查考验我。又过了四五个月,学校党的负责人牛英卿才找我谈话,并说明我在外边这一段表现得还不错,正式承认我的组织关系。
四、地下搞兵运
1928年4月,陕北特委正式成立,并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要求共产党员要打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杂牌军)中,争取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积极支援红军。
1929年冬,刘志丹到定边找到我说:“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搞军运工作吧!”我说:“组织决定怎干,就怎干”。他又接着说:“你们前一阶段搞得不错,斗争的很坚决,也很艺术。王子元新成立军队,我已经把你和吕振华介绍给王子元,你们就到他的部队去吧。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我表示同意。他又说:“那好,我就领你去见王子元”。当即,刘志丹就把我和吕振华领到王子元那里,并作了介绍,王子元说:“好嘛!我们懂军事的人不多,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冯玉祥那里来的,到这里好好搞,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就这样,连春节也没有过,我们跟随王子元部队开到了宁夏平罗姚伏堡一带。后来,我一直在王子元部队里搞兵运。1932年5月,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失败后,我从王子元部队到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搞兵运。新十一旅的前身是苏雨生的九旅。1931年春天,邓宝珊把石英秀部队整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任旅长)。当时,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1938年春,新十一旅又开赴榆林。当时新十一旅内部斗争很激烈,主要是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势力与顽固派的斗争。
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调防三边。旅部及一团驻安边、白泥井;二团驻柠条梁、堆子梁。1941年秋,刘保堂被三边武装土匪头子张廷祥、张廷芝设计谋*后,又围绕着旅长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三边分委和警三旅的支持,新十一旅地下党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让倾向我党的陈国宾当上了旅长,为1945年新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消灭张廷祥,夺回安边城
1941年9月3日,刘保堂派我到定边给新十一旅联系食盐。第三天,我正在定边西街理发馆理发,新十一旅一个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牛团副!张廷祥把刘旅长枪*了,并将连以上的军官全部扣押了。两家打了起来,情况很紧张,你得赶快回去。”我听了土兵的报告后,赶忙把发理完,跑到分委向高峰*汇报了情况。高峰听了又找来警三旅副团长廖纲绍等一起商量。最后,让我带一个骑兵连很快开赴安边。我说:“不用了,靠新十一旅自己力量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再派部队增援。”他们也表示同意。让我带了十几名换成新十一旅服装的战士赶到砖井。到砖井一打听,新十一旅已经撤出了安边,于是,我又赶到白泥井。高宜之、高昆山、朱子春、胡立亭等地下党员都在白泥井。当时我们就一块研究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打回安边去。但是,一、二团有矛盾,二团对刘保堂感情很深,为了争取二团的力量,我们打出了为刘旅长报仇的旗号,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并由我到二团做营长米杰山的工作,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我说:“咱们连个旅长都保不住,还互相闹什么意见,这样下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米营长认为我言之有理,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让我做了动员,大家痛哭流涕,一致表示决心为刘旅长报儿。
这时,曹又参营长也放回来了。于是,我又找他商量,让他当讨张指挥部总指挥,我和米杰山、柴明堂为副指挥。恰巧冯世光也被放回来了,我风趣地说:冯世光就是我们的“参谋长”,大家都同意这样干。在此之前,我秘密派汪兴民给夏品三、杜廷芝送信,让他们在新十一旅攻打安边时作内应,开东门放我进去。汪兴民回来以后,带回杜廷芝用麻纸写的4个大字“唯命是从”。这时,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要到定边亲自汇报,我也同意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冒雨在9月14日拂晓前赶到安边城东门。冯世光同警三旅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隐蔽在安边城西树林,隶属我们指挥,听候命令。我到东门后,让部队隐蔽好,然后悄悄走到城门跟前,让汪兴民跟夏品三答话。夏品三问道:“化东来了吗?”汪兴民说:“来了。”于是,就开了城门。我们很快上到城墙,向夏品三问情况。这时张雨亭(张七)带了两个哑巴警卫员过来了,并阴阳怪气地说:“品三,有什么动静?东门外好像来了些人!”我怕被张雨亭发现,立即抓过夏品三士兵的大衣和帽子穿戴上,跟着夏品三走到张雨亭跟前。夏品三一把抱住张雨亭,我说:“你抱着干什么,还不动手!”夏一枪打死了张雨亭,并解除了两个警卫员的武装。这时,张廷祥带了一群匪徒向东门冲来,我指挥部队顶了回去。张廷祥一看事情不好,即从北城墙跳下,跑到鸱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以后被抓回来镇压了。经过激烈战斗,除鼓楼和北城文昌阁未拿下外,其他据点都拿下来了。不多时,我调了两挺重机枪把鼓楼也拿下来了,只剩文昌阁了。我正准备叫高昆山通知用迫击炮轰文昌阁,不料,李友竹被副团长高乐亭哄上去扣作人质了。当时,我一边答应高乐亭的条件,放他们走,一边命令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埋伏。高乐亭放出李友竹以后,带着一伙人仓惶出城,结果除个别人外,高乐亭等人全被我俘获。到此,新十一旅胜利的夺回安边城。

在我们攻打安边的同时,委派柴明堂前往堆子梁提拿张兰亭、张廷芝父子。但是,由于柴明堂接受了张廷芝十几箱子贵重财物,便把张廷艺父子有意放走,给三边人民留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