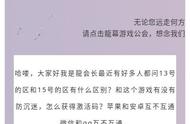柴房的门被推开,我听着响声轻轻睁开眼睛,带着些青蓝色的光顺着门的角度慢慢地淌进来,再流入我的眼睫里,完全睁开时,一个清瘦的黑色剪影出现在我眼前。
那人发须灰白,脸颊瘦弱,腊色的脸被冻出一层病态的红,眸子有点儿浑浊,青色上衣,灰色长裤,显旧的袜子和一双纳了很多补丁的鞋——是我的主人。
我从干草垛里慢悠悠地支起身子,对着他轻轻唤了一声,他笑着抚了抚我的毛发,将我身旁的竹篓提到背上,弯下身子打开我面前的栅栏,牵着系在我脖颈上的绳子走了出去。
外面天不太亮,风泛着灰蓝色的凉意,安安静静地掠过我的毛发,带着一阵冬天独有的寒冷与寂寥。
他拉着我到水槽边上,舀了些水下去,又放了一摞长长的甘草在旁边,取了水槽旁的斧子带上,我一边咀嚼一边看着那一抹青色在风里慢悠悠地颤,最后消失在山间的雾里。

他踏着逐渐消散的雾回来,放下装满木柴的背篓,在土窑旁蹲下,将窑上封住的口子开开,执着火钳慢慢地探进去,将已经封了七天的木炭一块块的夹出来,再将旁边叠在一起的竹篓拆开来,把炭放进去。竹篓装上推车,上面盖一只竹片做的封盖,用绳子牢牢地捆紧,再从推车上颤悠悠地爬下来。
我有些困倦了,事实上冬日的甘草并不好吃,草质疏松干瘪,嚼之无味。一口水下去,胃里便是凉的发苦。
那人喝了些水便坐在一个土包旁编起竹篓,一圈一圈地编。
土包是一个女人睡觉的地方,她特别懒,已经睡两年了。每天主子都要叫她起床,但她从来都不回答他。

“老婆子,你看我竹篓编的可快吧,不过肯定没有你快,村里人都想你的竹篓子,今天炭已经装好车子了,明天就去卖啦,希望天气冷一点好卖些,阿牛的状态最近不太好,应该是草太硬了,家里娃子改明儿不知道能不能打仗回来……老婆子,你在那边注意身体……”
主人的话总是各种话串在一起,但是并不刺耳。
天很快黑了,他只吃了几个硬邦邦的馒头便将我关进柴屋,屋子里隔了一小块地让我休憩,周围都是堆着的木头,我在屋子里常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吃食,不然怎么每天都只吃一点点,虽然那白色的团子硌硬,但那女人在时他总是吃的很多。
晚上睡的不太好,因为夜里风不知怎么得刮得很大,吹得门吱吱呀呀地响,有白色的飞沫从门上的通风口飞进来,舌尖碰到的时候,它就融成冰凉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