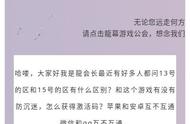第二天主人很早就把我带出去,让我拉着车子向着城镇的方向走,一整车的炭实在是有些负重,他也不急,只是带着我一路碾过冰面和雪地,入眼皆是白茫茫,他戴着一顶竹子编的宽檐儿帽,一手摁着帽子一手拉着我颈上的绳子在风里行进。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只是感觉太阳终于从山谷里睡醒,却是烈阳,照的人牛俱疲,汗流浃背,加上白茫茫的雪将光抛得亮如镜子,实在疲累极了。
主人将我身上的绳子卸下去,车子置在旁边的树身上,他坐下去,身形显得佝偻而脆弱。
前面是一片腐烂的黄泥地,狰狞又散发着恶臭。
两匹马上面坐着一黄一白两道身影,由远及近,轻快地踏着步子过来,经过泥地时,蹄上沾了一片脏污,那马匹厌恶地往下一瞥,眼神掠过我时不屑地哼哼几声。两匹马筋骨健硕,应是比我年轻许多,也是养尊处优者。
我并不想去和它争辩,但身旁的青色身影却有些颤抖。

两匹马围住我们,戴着一顶黑色帽子的黄衣身影从怀里掏出一卷纸来撑开:“皇帝有令——集物宫室也——”他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带着浓厚的女气,阴阳不分。他坐在马背上俯视着主子的眼神也是既带着蔑视又充斥着狐媚之意。
黄衣的收了卷子,白衣的便从马背上翻身而下,将车绳又往我的身上一系,主人欲言又止,眼中惊恐,却是强压了惧意颤颤地挡在了我前面:“官老爷……”他不知道说什么,竟然直接跪倒在地上。
“我就是个讨生活的……能不能……”
白衣的踹了他一脚,斥道:“死老东西,起来!”
主人身形有些颤抖,却是不起:“官老爷……您就放了我吧……”
白衣从怀里扯了什么东西出来,往我脖颈上一甩,我只觉得上边落了层雾,轻轻盈盈的。但心里却是苦涩得很。瞧着主人那蜷成一团的样子,实在是有些窘迫,便轻轻地唤他一声:“哞——”
主人回头望望我,没有笑,只是支着身子慢慢地站起来,裤腿上一片污泥。

“去*的死畜生,走了!”白衣的往马背上一跃,他黑色帽子后边的两片黑布便颤了颤,我不想听他的,主人却是回头对着我苦涩地笑,我只得从了他。
耳旁的喧闹声越加清晰,前面两人只是昂着头骑着马经过,人群突然变得静默而嗫嚅,纷纷散开,像用手拨开了水流。一个小孩拿着一个木制的鸟在街上跑动,不小心拦住了两匹马的去路,白黄两人却是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驱着马向前,速度不快,却是一脚绊倒了那个小崽子,她跌坐在地上愣了一会儿,欲要哭泣,一个女人便眼疾手快的将她抱走,应是她的母亲。
小孩子的木头鸟落在地上,伸着肉乎乎的手要拿,母亲把她摁在怀里头,轻声呢喃。马的蹄子再次落下,第二匹马的蹄子接踵而至。
木头鸟被踩碎成片。
我继续向着前方走着,背后是崽子的哭声和女人轻声软语的安慰声。我的眼眸低垂,不愿再想,主人在我之下慢慢地走,他的发丝苍白而老旧。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只是觉得眼前人停下,有几个灰袍的小厮围着我将炭卸了下来。
白黄两人下了马,眼神投向我。黄衣对着白衣耳语几声,白衣便踱着步子向着主子走来。扔了两匹红绫给他,又将我颈上的雾扯下来——也是红绫,揉成一团扔给我的主子。
“老头,你这牛——”
白衣的笑起来,“看起来不错啊。”
主人的神态本已是空洞,却应这话震得回过神来。
他仓促地呼吸着,“官老爷……您就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家吧……”
“别不识抬举——”白衣在主人旁边压低了声音,我却听得真切。
主人又跪下去,他实在是老了,没有力气去争辩什么,只是不断地磕着头,和石头地板的撞击声清晰可辨。
白衣的欲要叱骂,黄衣者却是将他制止住,饶有兴致地看着主人磕头,招招手让小厮把车推走,转身离开,白衣的回身吐了口唾沫,也跟着离开。
主人从地上爬起来,使劲爬上我的身子,瘫软在我身上。
我慢慢地将他驮回家里,村子里有人见着他的样子,去叫了村医过来帮他包扎伤口。
他从村医那里回来时一如往常,将我的门打开,带去吃甘草喝水,去山上砍柴,回来烧炭,只是总是怔怔愣愣的,望着远远的山脉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