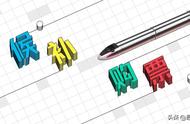作者:安颜颜
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不过,“学界通说”在这里与“大众文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顾炳鑫《屈原像》

江寒汀笔下的端午

崔护、程宗元《龙舟夺标图》局部

赵之谦《五瑞图》,故宫博物院藏

齐白石笔下的端午
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诵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纪的渡口回望历史,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要比人们想象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未见屈原:从《夏小正》到“恶月恶日”
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
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能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一端是精英阶层的“礼”,一端是普罗大众的“俗”。
“礼”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礼”,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据《夏小正》载,夏代已确定“两至”,所谓“时有养日” “时有养夜”,“养”为 “长”,“养日”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
通过《后汉书》可知,在汉代,夏至前后需要用 “朱索” “五色印”作为装饰,其原因在于这一天 “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所谓 “夏至一阴生”,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夜渐长,在阴阳家眼中这是“阴进而阳退”的体现,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扶阳抑阴”。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 “阴气萌动”的日子,而汉代“兼用”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
为什么是五月五日?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 “恶月恶日”。“恶月恶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这一日需 “蓄兰沐浴、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说明“恶月恶日”早在夏代就已滥觞。不过“恶月恶日”真正的影响在于其如魔咒般的习俗。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 “暖气始盛,虫蠹并兴”,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凡妇人因暑月产乳,取凉太多,得风冷,腹中积聚,百疾竞起,迄至于死,百方疗不能瘥”,王充《论衡》言: “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在中医观念中,妇人在产褥期极怕着凉,往往 “浓铺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中的“扶阳抑阴”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琐碎录》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配药的良日。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 “端午=夏至 五月五日”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
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 “夏至”这一条目来记录,如明代《绍兴府志》载“夏至……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
也因此,褪去龙舟的热闹、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
既见屈原:“诗人节”背后的端午再构建
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祛病除灾”的说法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
朝鲜半岛、日本自古使用中国农历,在这一历法体系中,也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夏至与五月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因而谱写出端午的另外两种可能:“江陵端午祭”和 “男孩节”。恰如屈原这个“中国式”的意外,缔造了中国今天的端午。
在没有屈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端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那在中国,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又是什么样的呢?
《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中虽然提到了龙舟和粽子,但并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与端午“牵上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言:“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续齐谐记》本是志怪小说集,正史对屈原逝世日期语焉不详,从屈原绝命词《怀沙》的内容直指孟夏时节来看,屈原可能逝世于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水。 “端午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论断,自然难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考虑到文献记载与历史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屈原与端午的 “邂逅”很可能发生于六朝时期。不过这一“邂逅”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端午还有纪念勾践、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传说——于是中国端午的问题其实不是为纪念谁而设,而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的纪念对象。
然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气质才华的确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但这个前提是中国古代端午确实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但事实上却是,端午习俗直到明清时期依然以祛病除灾为主,借各类药物驱除瘟疫的期冀,要远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续齐谐记》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纵然为真,也只是屈原与端午之间一场很偶然的 “邂逅”,而屈原与端午真正“结缘”的历史,不过百年。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依俗将 “屈原殉国日”设立为 “诗人节”加以纪念,并在第二年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节虽名为诗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节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再构建,屈原与端午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大众视视野中生根发芽。1953年屈原被列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艺报》在社论《屈原和我们》中更将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
随着屈原地位愈加崇高,借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便愈顺理成章。2008年,四大传统节日终于从民间走入官方视野,成为四个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国端午节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节日习俗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沉淀、变化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于是,近代文人崇敬的爱国诗人屈原,与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个忠君谏臣屈原成为一体两面;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端午节在经历了“屈原殉国日”与“诗人节”后,为千年前的那个端午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涵。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祛病除灾”的说法则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而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而《续齐谐记》中的惊鸿一瞥,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历久弥新。(安颜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