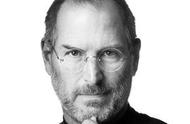《顺天时报》刊登的投票结果
白云苍狗,风华渐逝商细蕊也好,梅尚程荀也罢,能红透了天,是时势的造化。若不是民国之前两年,也就是1909年,“通天教主”王瑶卿首开旦角挑班的先河,旦角的出头之日还不知要晚来多少年。作为九流之末,做伶人本就不容易,男旦尤艰。军阀欺侮男旦,新派文人攻击男旦,陈独秀、鲁迅讽刺过梅兰芳,钱玄同管小嗓称“猫叫”,郑振铎说男旦是“人妖”,甚至有时还被怀疑是同性恋,老舍的小说《兔》便隐晦地写到了这个。就像宁九郎对商细蕊说的:“唱戏唱到这个名气,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恨着你的,就是有求于你的,知己无二三。台上是帝王将相,台下是九流之末。这一生庄周梦蝶,两厢皆妄。”

王瑶卿(左)、王凤卿(右)之《四郎探母》
男旦之难还在于舞台生命的短暂,青春一过,声音有可能塌中——中气不接,底气不足,逢高不起,平槽而无立音,滋花冒嚎——身形也容易发福。若是唱生的、唱净的发福许倒没多打紧,旦一发福就看不得了。早年和梅兰芳齐名的有位王惠芳,两位并称“兰惠齐芳”。据徐慕云《故都宫闱梨园秘史》记载,王惠芳成名后喜欢架着大鹰进山,没多久风吹日晒,皮肤和嗓子都不行了。程砚秋跟商细蕊一样嗜食,后来人到中年便自然发起福来,加上本就人高身长,更为显眼,报刊谑云:“好大一个旦!”,甚至上海观众直接唤其“大阿福”。
太平日子尚难抵灾祸横生,更何况动荡时局、忧患岁月。1937年,抗战伊始,北平沦陷,城里的戏班子走的走、散的散,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西山务农,荀慧生义演资军,马连良“奉旨唱戏”、抑郁成疾。再往后十二载,连年战争,满目萧条,一片混乱,北平梨园生计弥艰,也显露着更剧烈的分化。待到1949,便是另一个时代,又一段故事了。所谓盛极而衰,京戏的黄金时代早已在不期然间远去了。白云苍狗,风华不再,倒应了商细蕊后来那出《凤仙传》的末了一句——
“百年分离在须臾” 。


来源:凤凰网读书
撰文 | 徐鹏远、侯磊、李牧谣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为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删除内容!特别说明,本站分享的文章不属于商业类别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