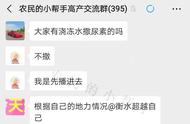王卓 教授
中国成长小说海外译介与研究现状及思考原文载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2年秋季刊
摘要:成长小说作为 “成长维度” 和 “教育维度” 高度融合、个人成长与家国命运互动共生的独特小说亚文类,其译介也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价值取向、文化基因和精神向度的对外传播。在中国文学 “走出去” 的大背景下,本文检视我国发展百年的成长小说的译介与海外研究现状,对比西方成长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提炼出成长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期为中国文学 “走出去” 中类型文学的规划和翻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建设性对策。
关键词:中国成长小说;西方成长小说;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
一、引言
莎拉·格雷厄姆(Sarah Graham)在其编著的《成长小说史》序言中曾言,任何读小说的人都最终会遇到一部成长小说——一种关于青年人面对挑战的成长的小说,“因为它是文学史上最流行、最永恒的文类”(Graham,1)。此言不虚。成长小说是以主人公的教育成长经历为情节线索的小说文类(王卓,2022:66),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本身的教育性(王卓,2008a:15)。尼日利亚女作家奇昆耶·奥贡耶米(Chikwenye O. Ogunyemi)曾言,成长小说在讲述他人的教育故事时也起到了教育的功能,“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主人公和读者都从此教育中受益” (Ogunyemi,15)。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成长小说在形塑人的精神、素养、情操等方面具有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成长小说的译介与传播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民族、时代价值取向、文化基因和精神向度的对外传播。而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其海外扩张、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不断运用的文化殖民方式之一。比如,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来华传教士着手译介了大量面向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西方成长小说,其目的是培养信仰基督教的一代中国儿童(宋莉华,1-14)。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方成长小说在中国的阅读 “热” 和研究 “热” 与中国成长小说在海外的接受 “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也是文学翻译与出版 “贸易逆差” 的一个典型例证。此种现象在中国文学 “走出去” 的大背景下值得深入思考,并亟须从中国成长小说的海外出版规划、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等多个方面制定出相应对策。
二、西方成长小说的中国 “热” 现象
西方成长小说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中国学界对其研究开展也很充分。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中国读者的启蒙外国文学读物就是成长小说。西方成长小说进入中国的历史已逾百年。一般认为1903年包天笑从日文转译的《三千里寻亲记》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成长小说,但如果把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考虑在内的话,成长小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至少还要提前50年(宋莉华,1)。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托马斯·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狄更斯的《远大前程》(The Great Expectation)、《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艾略特的 《米德尔马契》(Middle March)、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Jane Eyre)、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等欧美经典成长小说陪伴了很多中国读者走过生命中最宝贵的青葱岁月,而中国读者 “对其喜爱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自己的文学” (高玉,98-99)。
这些欧美成长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和这些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欧美成长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有几个鲜明的特点:1)引进中国早;2)翻译出版量大;3)译本多,其中不乏权威译者的译本;4)销量大,读者群体大;5)作品研究和译本研究深入。
以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在中国的传播为例。1908年翻译家林纾就将该书引进了中国,中译本的名字是《块肉余生述》。1947年,上海骆驼书店出版了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白话文全译本。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包括1980年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2012年宋兆霖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等。该书在长达100余年在中国的传播中,先后有20多个中译本,出自40余位译者之手。这部小说一直是中国读者的心头好,读者的阅读热情长盛不衰。以“豆瓣网” (www.douban.com)为例。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这一话题在话题小组和读书频道均受到广泛关注,有1000多条话题和评论。网友 “琪琪99” 说:“狄更斯用平淡朴实的语言讲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勾勒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大卫的人生在他找到姨奶奶后彻底改写,他身边那一个个纯真又高尚的人塑造了他、成就了他。‘永不卑贱,永不虚伪,永不残忍’ 正是他赢得他人喜爱的根本。” 这部小说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译者,林纾曾言:“迭更斯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 (1-2)。而林纾翻译的狄更斯同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狄更斯小说的独特魅力加上林纾优美的译笔,使林译的狄更斯小说成为现代许多作家的教科书。中国现代作家中有很多人是通过林译小说接触到狄更斯的,如冰心、沈从文、钱钟书、老舍、张天翼、矛盾、巴金、萧乾、王蒙等,他们都曾表示非常喜欢狄更斯的作品。” (童真,161)
再比如对中国几代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成长小说《简爱》。被视为女性成长小说的 “革命性的开端” 的《简爱》是中国女性觉醒和成长的启蒙读本(Showalter,122)。新中国成立之前,该书有3个重要译本,分别是周瘦鹃的《重光记》(1925)、伍建光的《孤女飘零记》(1935)和李霁野的《简爱自传》(1935-1936)。其中李霁野的《简爱自传》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该译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再版和重印,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新文艺出版社加印李霁野的译本共16000册。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印了3000册。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简·爱》的各种译本达百种之多(蒋承勇,11版)。
不仅是19世纪英语成长小说在中国读者甚众,影响深远,20世纪的成长小说同样拥有众多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比如,创作于20世纪初的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我国就有20多个中译本。该书出版于1916年,几乎同时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1933年,费鉴照在《文艺月刊》发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介绍了该书(951)。1980年台湾译者李文彬、黎登鑫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1983年中国大陆诞生了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
欧美成长小说不仅成为广大中国读者的阅读文本,也走进中国的教育体系,成为教材或者学生的推荐阅读素材。还以狄更斯和他的成长小说为例。著名作家、翻译家谢六逸曾指出,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的学校很早就被当作文学读物和教材(63-70)。商务印书馆1905年推出的《帝国英语读本》就收录了根据狄更斯作品改编的阅读文本;1910-191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 “英文文学丛书”,1918年又推出了《英语模范短篇小说》和《英语模范读本》,这些选读都收录了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故事(龚玲芬、叶峰,83-85)。新中国成立以后,狄更斯的作品更是走进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英美文学教材,也走进了中学的语文教材。网友 “百年_Sylvain” 就提道:“第一次知道《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还是在新课标语文教材上得知的”。这些欧美成长小说对中国读者起到了知识拓展、跨文化交流、教育和启蒙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但教材和文学读物中,外来作品占据优势,对我国青少年和儿童未来的审美观、文学观、价值观的培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构成的显而易见的 “文化安全隐患” 也应引起重视(姚建彬,6)。
除了业已形成的欧美成长小说在我国的翻译和阅读热潮,我国学界对成长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欧美成长小说研究专著的出版主要集中于21世纪的头20年。2004年,芮渝萍出版了《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孙胜忠的《美国成长小说与文化表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王炎的《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问世;2008年许德金的《成长小说与自传:成长叙事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王卓的《投射在文本中的成长丽影——美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芮渝萍、范谊出版《成长的风景——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张国龙出版《成长小说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侯金萍出版《华裔美国小说成长主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贺赛波出版《民国时期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中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孙胜忠出版《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西方成长小说文本解读》(商务印书馆)。此外,以西方成长小说研究为焦点的博士论文也呈现出稳定的热度。张军的《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影响作用研究》(2012)、宁云中的《空间下的主体生成: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研究》(2013)、买琳燕的《从歌德到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研究》(2021)等均是该领域的博士论文。除成长小说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我国学者的成长小说研究论文也硕果累累。根据CNKI数据库统计,截止到2022年1月份,以 “成长小说” 为关键词检索,共有期刊论文1488篇。这些论文主要聚焦于英美成长小说的叙事特点、人物类型以及主要代表作品的文本解读等,对欧美成长小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与世界文学领域对欧美成长小说的研究保持了对话性。
三、中国成长小说的海外 “冷” 现象
相比之下,中国的成长小说在西方的海外译介与研究却显得冷清、寂寞得多,对 “西方文学以及西方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 更是微乎其微(高玉,98-99)。尽管成长小说的概念源于德国,发展于欧美,但中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类别。有中国学者言,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因缘际会,几乎在一个世纪内经历了西方成长小说300年的所有变化过程(徐秀明、葛红兵,92)。而成长小说之所以能够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迅速结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成长小说,与中国文学基因中饱满的 “教化” 因子不无关系。中国的 “诗教” 传统由来已久。自孔子提出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以来,“在华夏文明之中以诗歌来抒情教化的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中教育主题的逐步形成” (钟今瑾、程方平,123)。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教育思想贯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雏形的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传奇、宋元时期话本、明清时期章回体小说的整个发展史中。清代以后,从李绿园发表《歧路灯》到包天笑应邀在《教育杂志》上连载教育小说,典型的中国教育成长小说开始出现(韩永胜,6)。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教育成长小说更为侧重教育维度,因此称为“教育小说”更为贴切。如1904年创刊的由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和1906年创刊的由吴跃人等人主编的《月月小说》,都曾刊登过 “教育小说” (韩永胜,6)。然而无论是教育小说,还是成长小说,其塑人、教化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成长小说更是“梁启超们”用以塑造新人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樊国宾,26)。
20世纪是中国成长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了一系列小说佳作。叶圣陶的《倪焕之》、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茅盾的《虹》、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同》《牛天赐传》、巴金的《家》、鹿桥的《未央歌》、杨沫的《青春之歌》,刘心武的《班主任》、曹文轩的系列青少年教育成长小说等均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然而我国的成长小说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却差强人意。在译介方面,我国的成长小说存在外译数量少、国外读者少、国外出版社规模小、影响力小等问题。在研究上则主要体现在国外学者关注少、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等问题。
以被认为是 “真正意义上” 的中国成长小说(李杨,95-102)——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小说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在中国的发行量超过五百万册,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成长小说。在国家的大力助推下,1960年该书的日文版出版,1961年朝文版出版,1964年英文版出版,迄今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覆盖了欧美等国和亚非拉地区。该书在海外的 “关注群体均以高校研究机构学者和汉学家为主” (李先慧,24),但关注量很小。李先慧在《<青春之歌>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文中查询了Goodreads,对英文版《青春之歌》的海外读者接受情况进行了统计。从2010年8月到2017年5月,只有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加拿大和美国的17位读者参与了打分,仅4人有文字评价。国外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该小说的论文的研究视角大多聚焦于意识形态问题,且多集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讨论小说中的青年人形象的只有两篇,一篇是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中的青年与老年形象》(“The Image of Youth and Age in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另一篇是中国成长小说研究专家宋明炜(Song Mingwei)的《青年人的驯化》(“The Taming of the Youth: Discourse, Politics, and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in the Early PRC”)。宋文将该书明确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成长小说。
如果说《青春之歌》作为 “十七年文学” 的经典作品,与西方读者之间存在着时间、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距,影响了小说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那么被称为 “中国罗琳” 的杨红樱的 “马小跳” 系列国内外接受情况的反差更需引起我们的反思。毫无疑问,“马小跳” 系列的国内销售获得巨大成功。国内总销量达到一千万册,连续41个月位列童书销售榜。然而,“马小跳” 系列英文版的8本书于2008年由Harper Collins出版社在欧美国家推出后,5年之内已全部停印。而读者反馈更是少的可怜,在英国版Amazon上只有一条评价(罗贻荣,57-61)。如果把杨红樱的 “马小跳” 系列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罗琳的 “哈利波特” 系列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反差考虑在内的话,这个文学界的 “贸易逆差” 典型案例更是触目惊心。“哈利波特” 从2000年走进中国,在20余年中售出三千多万册,“哈利·波特” 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达到17个亿(朱蓉婷,GA10)。
我国成长小说海外译介情况如此,海外研究情况也不乐观。国外成长小说研究的权威作品,如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世界的方式: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1987)、莎拉·格雷厄姆主编的《成长小说史》等均未提及中国的成长小说。尽管苏珊·豪(Susan Howe)等 “世界多元论” 学者坚持认为在德国之外存在一个强大的成长小说传统(Iversen,26),但他们似乎也从未主动在中国文学中寻找这一文学传统。这一点和世界文学界对非洲成长小说、加勒比成长小说越来越聚焦的目光相比,形成了令人焦虑的反差。
目前海外对我国成长小说做的最全面的研究是旅美学人宋明炜的《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1900-1959)。该书于2016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出版。这部专著是基于宋明炜2005年完成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青春万岁:国族青春重塑与中国成长小说,1900-1958》(Long Live You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 1900-1958,2005)整理完成的,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华语文学研究专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认为,该书不仅讲述了成长叙事在20世纪的中国如何演化的故事,还通过这一进程,勾画了一个现代中国本身复杂的成长故事。斯坦福大学威廉·哈斯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王斑(Wang Ban)认为,该书勾描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自我塑形的旅程,而该书最大的突破在于把成长小说编织到中国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追求之中。此外国内外学者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王璞等也有相关评论或者书评。在笔者看来,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包括叶圣陶的《倪焕之》(1928)、茅盾的《虹》(Rainbow,1930)、巴金的《家》(Family,1931)、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Children of the Rich,1945-1948)、杨沫的《青春之歌》(The Song of Youth,1958)、王蒙的《青春万岁》(Long Live Youth,1979)等中国经典成长小说完整、系统地呈现在西方学界面前,并尝试确立一个中国成长小说的文类谱系。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构建了青年人的 “成长” 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命运和现代性之间的独特的同构性。此外宋明炜的《在现代中国发明青年》(“Inventing Youth in Modern China”)一文收录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新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中。该文聚焦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散文《青春》的诞生和内涵,并着重阐释了该文如何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青年文化以及成长小说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等问题(Song Mingwei,2017:248-253)。
宋明炜的《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英文为写作语言、由国外出版社出版、以20世纪中国上半叶的成长小说全貌为研究主体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几部海外华人学者的博士论文也从成长小说视角审视了中国文学作品。2007年,Li Hua完成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动荡年代的成长:苏童和余华的成长小说》(Coming of Age in a Time of Trouble: The Bildungsroman of Su Tong and Yu Hua)。该文于2011年由布里尔出版社出版,题目改为《苏童和余华的当代中国小说:动荡年代的成长》(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Su Tong and Yu Hua: Coming of Age in Troubled Times)。该研究把苏童和余华两位当代作家的作品视为文化隐喻,反思了 “文革” 期间中国青年的成长问题(Li Hua)。该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拓展了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研究疆域,即以成长小说理论审视中国当代作家,思考文类和中国文学个体作品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中国的成长故事以独特的人物、情节和叙事丰富了成长小说文类,为中国成长小说融入世界成长小说家族开启了一扇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被作为成长小说的定位。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李前程(Li Qiancheng)的专著《悟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红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的文章《离开花园》(“Leaving the Garden: Reflections on China's Literary Masterwork”)等均对《红楼梦》作为启蒙和成长小说有所阐释。2008年Ma Ning完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从物质到浪漫的利己主义》(From Material to Romantic Egoism: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Novels, 1550-1859)。在该文的第三章,作者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进行了个案对比研究,该研究从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视角,基于《红楼梦》中自我和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构特点将小说定位为中国成长小说。
此外还有一些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提及了中国成长小说。比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汉学家白培德(Peter Button)在他的《中国文学和审美现代性中对 “真实” 的构造》(Configurations of the Real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2009)一书中,聚焦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文本,并特别从现代成长小说中人的主体塑形教育(bildung)和现代美学话语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审视了《青春之歌》(1959)和《红岩》(1961)两部作品。
以上梳理表明,中国成长小说海外研究总体数量偏少,且研究者多为海外华人学者,研究对象多聚焦于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对当代中国成长小说鲜有关注。此种情况和我国对欧美成长小说研究体量大、研究群体大,研究方法丰富、多元,对英美当代成长小说追踪及时等特点形成了较大反差。
四、中国成长小说
“走出去” 的多维意义与对策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主要局限于学术层面” “如果说中国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已走向了大众层面的话,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尚处在小众范围” (姜智芹,36)。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成长小说的中国 “热” 和中国成长小说的西方 “冷” 其实正是此种中西方文学 “贸易逆差” 的一个缩影和典型案例。只不过和其他中国文学作品——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外译、中国典籍外译情况相比,中国成长小说的 “逆差” 现象更为明显。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 战略的优选路径与重要内容(陈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一项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伟业(姚建彬,1)。21世纪以来,国人在 “走出去” 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胡安江、梁燕,69),但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现象依旧存在。
作为独特的小说亚文类,中国成长小说 “走出去” 具有不同寻常的多维意义。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长小说 “走出去” 具有中国文化传播的普遍意义。尤其是考虑到成长小说中有很多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其 “走出去” 的意义就更不容忽视。然而成长小说本身具有的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其 “走出去” 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成长小说 “走出去” 的特殊意义在于该亚文类 “成长维度” 和 “教育维度” 的高度融合性(徐秀明、葛红兵,82-93)。这种文学形式通常试图教会读者理解他们当下和过去的情感、成长和归属的过程,在最经典的成长小说中,教会读者成为“公民”的模式是小说文本的主要内核(Buckley,18)。成长小说独特的教育、教诲目的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的传递和人格塑造功能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都不具备或者难以完全实现的独特功能。成长小说的人格塑形功能从该词的构成就清楚地表达出来。“Bildungsroman” 中的 “Bildungsroman”一词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Bild” 是 “形象,图像”,既有 “VorBild”,也就是 “范本” 之意,又有 “Nachbild”,也就是 “摹本”之意。总体而言,这一词的含义就是按照范本进行摹写,按照某种既定的理想进行教化或陶冶(迦达默尔,22-25),是主体主动地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张颖慧,44-47)。成长小说显化的教诲(王卓,2008b:73-74)、教化功能使得该文类能更为充分地传递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情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这也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 的重要使命之一。
其二,该文类带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塑形的功能。成长小说在线性或者非线性地记录下主人公与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得认同的过程中,还承担着与主人公生长其间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协商的使命。成长小说不仅涉及人的身体成长和情感成长,还深刻地触及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协商、互动关系。正如阿波罗·阿莫科(Apollo Amoko)所言,成长小说聚焦于年轻的主人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的塑形(Amoko,200),因此成长小说中的个人成长往往也是国族重构的隐喻,涉及个人成长与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等的复杂的互动关系(王卓,2021)。就像莫雷蒂所言,成长小说 “不仅在小说史中,而且在我们整个文化遗产中” 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随着我们阅读这些小说,它们 “描写并重构了与社会整体的关系” (Moretti,23)。中国的成长小说,尤其是现当代成长小说表达的是中国对民族性、现代性的建构和阐释,在当下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背景下让国外充分了解我国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底蕴以及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其三,成长小说的读者群体既有青少年,也有成年人。事实上,无论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还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抑或是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Lord of the Files)都是很多成年读者的阅读保留书目。究其原因在于,成长小说的 “大致轮廓” 往往都涉及从童年到成年的转化(Buckley,17-18),而叙事也往往是在童年和成年的双重视角下展开的(王卓,2008b:73)。比如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福楼拜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1869)中,主人公大卫(David)、皮普(Pip)、弗雷德里克(Frederic)都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某种社会角色:大卫成为令人尊重的作家和记者,皮普成了伦敦的绅士,弗雷德里克最后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成长小说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读者群体的多元,而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体意味着成长小说具有其他文类所不具备的强大的传播面向和传播力度。
可见,作为价值独特的小说类型,成长小说 “走出去” 的意义十分重大。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文学 “走出去” 过程中,加强文类的规划。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文学 “走出去” 中存在的弱项。很多 “走出去” 的中国文学也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如德国翻译家郝慕天说:“在德国,一本中国小说的出版,仅仅是源于一次巧遇或一种尝试。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对作家、文学流派的选择随意性较大,对同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也缺乏系统性。”(转引自刘莎莎,B01)事实上,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文学 “走出去” 过程中文类和文本选择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马新强认为,在文本选择方面,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时代性问题,同时还要兼顾作品的题材和体裁(89)。陈伟也认为,“从文本选择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外译需要注重世界话语,同时更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此就要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向世界推介并阐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华思想文化与民族智慧的故事或作品,它们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材料”。
基于此,应对文学 “贸易逆差” 的对策之一就是规划、丰富、设计推出去的中国文学类型。目前更多学者和图书市场将着眼点放在了中国谍战、科幻、悬疑小说的海外译介。此种选择无可厚非。尤其是随着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解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等成功地走向海外图书市场,海外也出现了中国科幻小说、密码小说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同样作为类型文学作品,成长小说 “走出去” 的规划和推介力度明显不够。事实上,成长小说恰恰是应该着力推介的中国文学类型。这一小说亚文类所承载的个人成长和国族构建的文化基因使得它能够更为充分地既反映个人情感又勾画群体和民族命运,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事实上,中国人的个人生活、思想以及中国的发展变化才是很多海外读者真正感兴趣、想要通过文学阅读了解的内容。将成长小说定位于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徐秀明、葛红兵,91)的曹文轩作品外译取得的不错的成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姚建彬,6)。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载的成长小说发展史独特的演变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的国民成长史和民族奋斗史。无论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 “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和革命写实叙事模式”,还是80至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图景(徐妍),抑或是21世纪的头20年成长小说越来越明显的类型化特点和越发独立的美学特征,都从多个层面反映了这70年国人成长历程的独特性和国家建设与人的成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文学外译应充分发挥成长小说的独特功能,“通过这些作品中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现实状况的了解,扭转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基于历史形成的片面认知,消除其对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误解”(马新强,89)。基于此,笔者建议以文学类型为基础,策划中国成长小说外译项目。此种模式的外译的一个优势是,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和读者期待。同时中国成长小说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又有着迥异于西方成长小说的美学特征和叙事特点。相同点是文学对话的基石,差异性是碰撞、质疑的火种,而基于对话和问诘的文学交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
除了宏观层面按照亚文类来规划外译项目外,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成长小说也有其 “特殊性”(黄佳佳、徐德荣,95)。成长小说明确的教育、教化目的以及文本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精神向度等内容要求其翻译策略应该凸显 “翻译文本的认知和批评功能”,从而起到文化和知识的 “掮客” 作用(西蒙,283)。这也是斯皮瓦克倡导的 “知识性的接受” 的翻译策略,其翻译文本常常带有序、跋和注释等组成部分(西蒙,283)。此种翻译策略在中国文学外译中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诗经》英译、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G. Graham)的《晚唐诗》英译都加了长篇序言,阐释文化背景和翻译理念、策略选择等。与其他类型文学作品的外译不同之处在于,成长小说的外译更应该通过文化翻译策略,强化传播和教育功能。中国译者在翻译西方成长小说时承担起强化成长小说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成功案例不少。比如潘帕翻译的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 · 希斯内罗丝 (Sandra Cisneros,1954- )的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984)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小说译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译者为小说文本加了50个注释。这50个注释参与了译者翻译的全过程,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而且是对这部成长小说 “体裁” 以及小说的 “教育功能” 进行 “显化处理” 的有效手段(王卓,2008b:73-74)。这一翻译策略值得我国成长小说 “走出去” 过程中的翻译实践进行借鉴。
五、结语
在中国文学教化传统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双向维度中 “成长” 起来的中国成长小说是传递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情感、道德、审美、价值的完美载体,在中国文学 “走出去” 背景下,中国成长小说海外译介与研究具有独特的文类价值。然而要想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亚文类的国际传播力,我们既需要在宏观上做好外译作品的文类规划、作品文本规划,按照文类系统地推出中国文学作品,也需要在微观上注重成长小说翻译策略的选择,凸显成长小说的文类特点,强化其教育功能,而这也是我国建设中译外翻译话语体系和翻译话语资源的重要策略之一(耿强,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