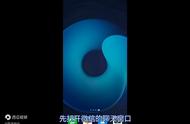换句话说,“音乐有无好坏”这个论点的意义本身需要架构在所持者的立场之上,在资本介入以前,“喊麦”也许仅仅是小镇青年的一种“发声”渠道,是不是音乐、是不是好音乐并没有人关心;而在“喊麦”成了资本和商业利益圈定的对象之后,“喊麦”也成了人们消费的对象,也势必会不断地出现在主流市场的视野之中。
结语
2016年,MC天佑在接受《中国青年》采访中曾说道:“你不认可喊麦,至少不要歧视,大家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我见过我们屯里有耕地的,耕累了站在那旮旯,对着太阳唱个二人转,没见过谁会唱首《我的太阳》;吃完饭老百姓都是遛个弯扭扭秧歌,没见过谁跳芭蕾。我就是地里长出来的李二狗,长不到瓷砖里,只是我能听到底层人的真实呐喊,替他们唱出来。”“底层人的真实呼喊”,这是MC天佑对自己喊麦行为在社会文化地图中的定位。

而“喊麦”等一系列底层表演向主流话语权的冲击,也正如秧歌与芭蕾、二人转与意大利歌剧,其预示的是社会底层与中产阶层之间巨大的阶级区隔和文化鸿沟。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到底该如何取舍?“喊麦”应不应该再多点在音乐上的提升?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也很难用上帝视角去回答。
《惊雷》为什么还会被追捧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无数的《惊雷》为什么一次次的刷新大家对音乐的认知?无论如何,音乐本无界限,但也不必毫无底线。但愿中国音乐圈下一次的集体狂欢,不会是又一次的惊雷之举。
参考资料
1.施蕾:《喊麦:阶层突围、消费权力与声音政治》,《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2.陈亚威:《底层表演与审丑狂欢:土味文化的青年亚文化透视》,《东南传播》,2019 年第 4 期(总第 176 期)
3.贾文颖、黄佩:《从快手App看小镇青年的精神文化诉求与扩大的数字鸿沟》,《东南传播》,2019 年第 12 期(总第 184 期)
排版 | 安林
本文为音乐先声原创稿件,转载及商务合作,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