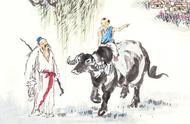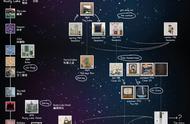这是杜牧的名作《泊秦淮》,其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句引人深思。乍看之下,杜牧似是在讥讽这些歌舞卖笑的“商女”们,竟不知国家沦亡、民族凄凉的痛苦,仍我行我素、歌舞卖笑。

然而这首诗的妙处,并不在于对“商女”的讥讽,而恰恰在于这个“隔”字。
“隔江犹唱后庭花”,与其说是讥讽,不如说是一种惋惜。诗人与这些歌女相隔一江,她们仍在欢歌,却不知隔岸的诗人正在伤怀,她们仍在卖笑,却不知那笑容背后是诗人百感交集。
这江水似乎成了时空的鸿沟,将欢乐与哀伤、歌舞与伤怀割裂开来,使两岸的景象成为强烈的反差与讽刺。“商女不知亡国恨”,正是这道鸿沟最好的注解。

然而这不仅仅是时空的隔阂,这“隔”字更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
公元884年,黄巢之乱平定后,唐僖宗李蛮被迫迁都于成都。此后二十年间,长安一度成为军阀混战的角斗场,城池破败,百业萧条,江边夜市也早已冷清,那些歌楼游女大多已散,少数残存者也恐怕难以欢歌自如。

二十年后,僖宗东归,杜牧也随驾还京。登上白帝城望长安,杜牧看到的却是满城疮痍。这十余年的战乱与动荡,早已使这个当年光辉灿烂的都城黯然失色。
这就是《泊秦淮》中的历史内涵。“亡国”二字,正是长安沦陷、国破家亡的写照。而当诗人泊舟秦淮,听到那遥远的歌声时,对长安覆亡的切肤之痛又如何能不顿生悲痛?

所以,这“隔”字中的苦涩,远不止是时空的隔阂,而是一整个王朝没落、一座首都覆灭的悲凉。
然而人生如梦,百年兴亡仅是过眼烟云;生死离别,亦是人世常态。这歌声虽不及当年妖娆多姿,也已蕴含动人之处:
这里不再有炫目的彩楼游宴,那些游女们也早已散去。余下这几个仍在坚持的歌女,她们也许并不像作者那样对长安覆灭心怀痛楚,她们也许并不理会这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只一味持续歌唱,似是要证明,尽管朝代更迭、沧海桑田,但生老病死的人世常态,始终未变。

她们歌声中所展露的,正是杜牧心头所未及的惬意。因为她们并不理会种种无常变迁,只是本能地歌唱,任轻歌曼舞。
而这也恰是杜牧听闻她们歌声时百感交集、唏嘘不已的缘由。
没有美人在怀,却有歌声相伴;
没有长安昔日繁华,却有秦淮永驻人间。

这就是“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蕴所在。
它不再只是对“商女”的讥讽,而是民族沧桑变迁惭愧之余,对那无知者仍能歌舞从容的羡慕,乃至人世常态的哀戚与释然。
一句“隔江犹唱”,道尽了太多故人离别后的无尽唏嘘,又道出了太多世事无常后的悲喜参半。这正是《泊秦淮》这首诗的深意所在,它超越了对“商女”的简单批判,而蕴含了更丰富的历史与人生体认。其妙笔只在一个“隔”字,却透出无限空灵与凄婉。
诗词揭秘: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缘分未尽,再次相会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