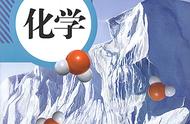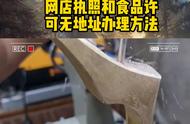以下为莫言的自述:
我的故乡是山东高密,按说高密人写的小说,高密人应该有很高的阅读热情,但事实上高密的农民读过我小说的人非常少,包括我们村子里的那些人也都没读过。
以前,我每次回乡他们都问我:“你在哪个报社做记者?”我说:“我在解放军报。”他们认为记者就是最厉害的人,是权力无边的人。
后来我离开部队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去《检察日报》做记者,也是受家乡父老乡亲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我回去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他们我是《检察日报》记者。
他们说:“哎呀,这个孩子终于出息了。”更老的会问我:“你现在是什么级别了?”我说跟我们县长差不多大了。“这官做得不小了。”所以说一个作家,在我的故乡农民心目当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988年,与母亲及朋友在老家的院子里
我最早的小说都来自真人真事。《红高粱家族》里有一个王文义,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我不但用了他的事迹,而且使用了他的真实姓名。本来我想等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是等我写完之后,改成无论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
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小说也在村子里流传。王文义看到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是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
我父亲说,他小说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个土匪种”,难道我是个土匪种吗?这是小说。王大叔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把我写死我不高兴。
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去看望他,也有个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我说大叔,我是把您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了一个大英雄。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有了”的大英雄吗?
我说后来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们儿也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听说你用这篇小说挣了不少钱?

1987年,在建筑工地
我的创作动机曾经非常低俗
我曾经请一对夫妻吃饭,结果那个丈夫不吃水饺,那个妻子不吃羊肉,我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我感到很抱歉,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不吃?
我创作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我五六岁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村的孩子像你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非洲儿童差不多:骨瘦如柴,腹部膨大。我们像小狗一样在村子里、田野里转来转去,寻觅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之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童年时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到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吃煤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
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