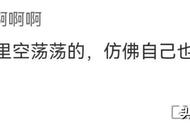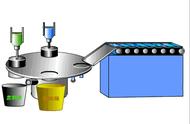没有敌人,我寂寞死了
王朔曾说中国当代作家都不及格,从韩少功到张炜,从贾平凹到阿来,他逐一放言点评,在他眼中只有几位及格。
作家写到最后,有一篇小说对得起自己,就是上上签了。有几个人最终能拿出东西来?
王蒙可以,张洁也可以,我觉得他们过去的作品,张洁比较灵敏,说实话,王蒙还有余地,他那人比他作品大,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张洁的文笔很精粹。别人吧,资质都不如他俩高。
知青作家里,王安忆当然甚高,她的短篇小说写得多好呀。
梁晓声,我觉得他也有戏,愤怒出诗人呢,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人。
张炜、韩少功都有可能,但韩少功写得够多了,《马桥词典》、《报告政府》、《山南水北》,演大师演得不太像了。
张炜非常有灵气,但要注意孔子就是一小学教员,修孔孟之道,没戏。
包括张承志,你别看他不吭声,他那一定憋着一个东西呢。
李锐在山西也可能“出来”。
但贾平凹装神弄鬼,玩笔记小说的路子,多可笑,那跟吹他的小气候有关系。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还好,但《废都》完全是扒厕所的东西,他真是颓废到无聊的程度,就别冒充“大家”了。
阿来的《格萨尔王》我不期待,看《尘埃落地》你都能感觉到他是跪着写祖先的文化。
铁凝、池莉、王安忆都是我姐姐。
池莉有个问题,她有一块“遮羞布”,总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关心劳苦大众,她内心那么多事,都没写。站在窗户那看看人家,写小市民,你了解吗?
她的作品有隔膜感,但我也就敢当着她的面说她的哪部作品是臭大粪,文人虽然当面不聊作品,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和她亲。她的中篇《一去永不回》可真好,剧本我都写完了,但被电影局灭了。
当年池莉已是一方诸侯了,她约了大家坐船游江,在船上,打了五天牌,我都和女的一家子,还老看她的牌,有人还为这猴急。
其实以前大家都挺好的,后来就是媒体瞎传话,大家也见不到了,一句话伤了人很多年。
你们摸摸良心,在外面,我是不是都照顾你们? 排队加塞从女的那加,都是我去; 走哪,没一会,人都跟我亲人似的。
我也喜欢敌人,敌人相当于你的反物质面,没有敌人,我寂寞死了。我假装谦逊,演得我累死了呦,你们还认了真了。
我给你们演道歉呢,这我他妈太占便宜了。
你是不是感觉受伤害了? 我这么大的腕,我说话呛着你了;我没错,也给你道歉呀;我小心眼,我爱攻击人,可跟所有人没仇。
中国人就是互相不信任。
作品没出来前,我还没那么自信,我必须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先锋派作家:
男的超不过胡兰成
女的超不过张爱玲
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他不敢坚持自己的路,然后想向现实妥协,又无处妥协,这是一个尴尬境地。
他当年那些小说是怎么写的?是学的吗? 如果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对不起,那你现在没得学,就瞎了。他的知识都过时了,完全和时代脱节。
他的问题不是皮太薄,而是更厚。
余华,他要不沉下来,就没戏。我还不知道他呀,《兄弟》根本不用看。他去美国晃了半年,这岁数了还跑出去看热闹,还跟人炒股票,患得患失。关键是他看不得别人好。
朱伟带着他发烧古典音乐,附庸风雅,说实在的,我老感觉,李陀给他带出毛病来了,一定要参和精英分子才有安全感,你犯得着吗?
余华,老强调虚构与现实,你跑不远,躺在屋子里是打不开内心世界的,得经历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边上看一眼。
你那点假泪无非是看完别人的东西留下的一点联想而已。那叫联想,行吗?
从《活着》开始,余华就被上海评论家排为和王安忆、莫言一排,你就跟着混吧,我看你露不露怯。
前者你写不过《活鬼》,后者写苦难,你写不过阎连科、刘震云这些有农村经验的作家。
你以为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哭,写出来就是苦难了?你无非是看到了个伤口,你知道痛苦是什么?
耍这种小聪明。你要想冲到前面去,对不起,没你的份。要么你回到南方,写点散文什么的。
叶兆言的才子文章写得挺好的呀,也是一路。
史铁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部好小说,自己写完就得了,别学别人,学了也没戏。
余华言必称卡尔维诺,犯得着吗?
余华是跪得最狠的,都跪出膝盖印了。你学别人,无非是高明的模仿和拙劣的抄袭,就这点区别。
人格都是依据环境形成的,看到环境就知道作家的格局有多大。但有一点,活得太舒服的人,没戏。
苏童、叶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协团结一气,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文章有闲适气、才子气、六朝气,小说也就一般般。
《碧奴》也就超不过什么。因为烦恼出菩提,你没有烦恼,哪里有觉悟?
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范儿的,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就超不过张爱玲。我就敢说这些话。
格非啊,我接触过,不太熟,没看过他的东西,我感觉他太像一个知识分子了,非常拘谨,个性偏软,但小说没有锋芒也就没了利器。
先锋派就是从西方文学学了点皮毛回来卖弄,非常不成熟,那些作家大多从大学生开始出名,那时大多还是文学青年,自我认识还没开始呢。
你要满足这个,那就永远长不大。说白了,先锋派在当年就是扯淡,在中国这个圈子里,那无非是翻译体的借鉴。
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你们无非是内心敏感点,处理的故事摆脱了现实主义讲故事的那条路,偏重了内心,与现实也有呼应,有点像印象派,但要说那就是先锋派,太没见识了。
不过是一群没有见识的评论家评论同样没有见识的文学青年。

我都不信这书是我写的
以前我写的呀,都是些感悟,就是散文游记,只不过我把它当小说了。
我已经经过自我否定、自我毁灭,把过去自己的东西全部砸碎,这才能绝处逢生。
我放眼的是宇宙。
以前说民族的是世界的,我说,个人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这些作家大多是些穷孩子。你们谁也别跟我比。
我装了多少年了,身为精英,我没有说,我是假客气。我等东西出来了,让你们看看。
当年刘恒说,小王,你摔个跟头就好了,果然。
以前,我爸是教战术的教员,家里挂的是世界地图,看的军事材料是电报,爱看的都是英国的间谍小说。欧洲史尤其是军事史,我烂熟于心。
那时看过《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兴亡》什么的,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搁脏心眼的地儿。
小时候我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书是《战略投降》,说的是当战败已然成定局,怎样投降获得最大的尊严和保全实力。
社会现实的苦难不用作家写,有纪录片和记者呢,作家的任务是转到内心,把人性最黑暗的拿出来。
我前一部小说就叫《在黑暗中》,写了一些悲欢离合、生活方式,现在不准备拿出来,牵扯到很多人的隐私。
《唯物论史观》相当于我自己写的道德经,本来是写给我女儿的,写着写着最后写成诗了。
《我的千岁寒》让汉语有了时态,全是灵性的文字,要说美文这叫美文,全是文字的菁华。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金刚经》写于两千多年前,因为那时的物理和化学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更多是观心。
其实反观和观天是一回事,现在物理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就拿物理这个利器追本溯源,这是把非常锃亮的刀子。
有的作家还从传统中找灵感,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你能不能从科学里找?
一些科普著作非常好,连历史和人的本质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得非常清楚了。
至于爱情,过去在我的小说里,从没有爱,只有少年情怀,但以后我会写爱情,我将把爱的兴趣写到审美甚至传奇的角度。
你们也别叫我大师,那也就一中级职称,你们也没能力伤害我。
我可怎么办啊?我必须,说话要和气,出入要小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