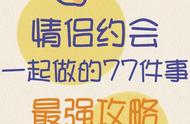姜文《太阳照常升起》海报
而到了张大磊、忻钰坤、杨瑾、李睿珺、毕赣、周子扬、蔡成杰等第六代之后的新一批导演不断问世的处女作中,一种原乡与诗性的表达,依然延续着这种现代性的追问与思考。
这类大多游离于主流院线之外、又能频繁出入国内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影片,逐步获得市场发行,进入“艺联”(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或全国院线放映。而更可观的是,像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总票房过亿、《南方车站的聚会》三天破亿的票房,说明导演和电影文本的国际化品牌,兑现了一部分商业号召力,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消费体量,说明新一轮年轻观众的电影感受力正在发生蜕变。
那么,刁亦男是如何跻身国内一流导演行列呢?
如果单从《白日焰火》去衡量,那还远不至于。《白日焰火》延续了他在《夜车》中形成的稳健构图和单镜头厚重的表意空间,故事层面也并没有让悬疑和人性的复杂,在国际视野的经典黑色电影中略胜一筹,但《白日焰火》黏稠的文学气质和对现实困局中生存的多边性描述,超越了惯常生活的认知逻辑,给观众提供了人的原罪与忏悔性救赎之间的想象空间。

《白日焰火》画面
特别是区域性的影像风景,营造了彻骨寒冷中“雪”与“焰火”两种“冷暖”对立的意象,都充满了极致的“白色”死亡与幻灭的悲剧感,而这种悲剧感在最后一场戏中的场景氛围和音乐渲染中,提升了观众浓烈的诗意感受。
刁亦男正是对这种“困局之人”的状态书写,突破了中国电影对个体求生本能和赋予形式感的影像表达,同时终于揭掉了那一层若隐若现的道德面纱,进入了真实内心体味的艺术探索之道。
如果说《白日焰火》对这种“困局之人”和“多边性际遇”的表达还不够彻底的话,《南方车站的聚会》让刁亦男真正进入国内一流导演的序列。这个片名让观众误以为是一个浪漫怀旧的故事,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血色浪漫”,而且引出了一个古老“血酬”的概念,即“兑命换钱”。由此,“聚会”就是“赴死”,就是以身犯险和自我成全,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

《南方车站的聚会》逃亡场景
民间的“血酬定律”,往往是在某种利益对抗中形成暂时性的对峙状态,一方以悬赏的方式,寻访技高一筹的*手或者帮助提供线索而尽快地消灭另一方。在利益驱动下,人性幽暗的一面开始*动,一切秩序被洗牌和重建,故事的情节和议题也有了突破各种伦理道德的既定边界。因为牺牲者往往只是一个牺牲品,其兑命的“血酬”也并不一定能送到利益关涉者手中,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内斗和更多无谓的死亡。
很多电影并没有将原始的血酬作为故事的核心概念,来发展主要情节,而是通过拓展、变形和延伸,再包裹上层层社会或文化内涵。比如“荆轲刺秦”的母题,在张艺谋的《英雄》中是被权利书写的。无名最后的“兑命”,换来天下的和平,其血酬作为抽象的“和平”输送给同样抽象的“人民”;《全民目击》中当司机查出自己肺癌晚期,甘愿为老板犯事的女儿顶罪,其“血酬”是为了偿还老板给予自己超额的工资待遇及感恩之情。
一般的血酬,基本都是由第三者来完成的,很少有个人为了不切实际的血酬而甘愿主动赴死的。但刁亦男叙事棋局的巧妙性在于,他给主人公周泽农设置了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一个过去五年当盗贼和混混的边缘小人物,虽然他有矫健的身手,但是在他误伤警察的那一瞬间,他并没有选择一个人逃亡,而是开启了灵魂救赎的望乡之旅。

胡歌饰演的周泽农
这个创新的故事设定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因此,不再需要过多的枝蔓去舒展故事的逻辑细节和人物前史。义无反顾的“回来”这一行为,就足以带动所有与主人公关联的各方力量的跃动,由此形成叙事的“局面”。
可见,刁亦男是深谙戏剧情境设置之道,而整个故事围绕车站和车站附近80年代的板楼,凝重的质感、多空间区隔的巷道以及脱落的墙皮,构成一个随时准备兑命的亡命徒的精神废墟底色——生于潮湿的市井,同样死于潮湿的河边。
而且连最后的晚餐都没有吃完,突兀而至的死亡威胁,竟然唤起了观众对主人公更大的移情效应。周泽农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点,增加了故事的悲剧意味,就像《*手莱昂》和《雏菊》一样,主人公都是犯了原罪的职业*手,但在剧情演进中,都成了观众移情的对象,这种魅力更多是来自故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