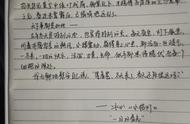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入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着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去。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XX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XX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见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倒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让我坐在炉前的小凳子上,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插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来,谢了她。她送我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接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了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候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
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有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文学艺术的使命在于创造出各式各样美的形象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冰心的散文《小桔灯》中的主人公小姑娘,是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而她的所言所行却无处不蕴含着内在的美 ——心灵美,情操美。作者通过精巧的、别开生面的艺术构思,十分真实而生动地刻划了小姑娘这一美好、感人的艺术形象。
首先,《小桔灯》之“美”,美在选材上能够“以小见大”,“平中见奇”。作者善于从看似寻常的事物中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从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冰心把山村小姑娘、不起眼的小桔灯、小姑娘照看生病的妈妈和做灯送客这些十分普通平凡的人、物、事,放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光明与黑暗正在作生死搏斗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上,从而开掘出“人民在受苦,也在反抗,在盼望,盼望着革命胜利的曙光”这一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主题。《小桔灯》只有一千五百多字的短小篇幅,却包容着如此深刻的寓意,真可谓是一篇玲珑剔透、回味无穷的散文佳作。
其二,《小桔灯》之美,美在立意的深刻新颖。作者选取小姑娘“打电话”、“照看妈妈”、“巧制小桔灯”等三件事,如果仅只表现小姑娘的“早熟、能干、心地善良、珍重感情”这样一个主题,也是能够成立的。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站在特定的时代的高度来挖掘这一平凡题材的深刻含义,揭示生活的真谛。因此,《小桔灯》的主题提炼得深刻而新颖。作者紧接着叙事之后的一段抒情文字,直抒胸臆,真切自然,是对前面叙事的归结和深化,是全篇的点睛妙笔。它深化了主题,对小桔灯的象征意义作了充分地揭示——小桔灯象征着蕴藏在革命人民心中的希望和火种,小桔灯就是光明和胜利之灯,正如鲁真在《春颂——评冰心的〈小桔灯〉》一文中所说:“当她(作者)感激地接过小女孩送给她的小桔灯时,她感受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这段文字有很深的寓意,她(作者)在寻找光明,这是她在美国的慰冰湖畔没有找到的东西,现在,她从一个穷苦的木匠的女儿身上看到了光明”。看来,这段抒情文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对主题的升华,是对主人公形象的升华,也是美的升华;它给了读者始料不及的新意。
其三,《小桔灯》之美,美在其结构处理的明暗相济。初读《小桔灯》,似觉其结构平淡无奇,但仔细推敲,则会发现它的精妙之处。冰心善于精心地组织材料,把各种材料都放置在最适当、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小桔灯》结构的突出特点,即是明线与暗线的互相交替运用,这种结构处理使文章增加了立体感,而不同于那种一般化的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的平面结构。“我”与小姑娘的交往,小姑娘的音容举止是明线,作者运用正面描写,始终让这一明线处于主导地位;小姑娘的爸爸王春林及一家人与医学院的学生的关系,则是暗线,作者运用了侧面描写,直到文章收尾,方令读者恍然省悟其中的奥秘。其暗线对明线起了陪衬和补充说明的作用。明暗相济,缺一不可,共同为表现主题服务。这种立体的艺术结构使全文平添了美感,使读者领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情趣。
其四,《小桔灯》之美,美在对人物形象的白描式勾勒。小姑娘是作者倾全部感情、着力表现的中心人物。在全文五分之四的篇幅里,作者运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抓住人物最富有特征的言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以寥寥数笔,便将一个早熟、镇定、勇敢、乐观、纯真善良、富于内在美的中国农村贫苦少女的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宛若塑像一般,很有立体感。她那贫寒的外貌,令人同情;“我”和她攀谈,进而感到她的懂事、可爱;“我”到她家探访,她沉静有礼地接待;她乐观地“笑谈”那寒酸的年夜饭,深思般地解释爸爸的下落;熟练、敏捷地制作小桔灯;热情地送客;特别是对光明未来的自信,……这一切,衣着、外貌、言谈、举止,都只有在“这一个”抗日战争年代的、饱经生活磨难的山村小姑娘的身上才能具备,再不能有第二个了。她是那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感情,她的形象仿佛开放在荒野中的一朵散发着清香的野菊花,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作者那一段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文字,更把小姑娘的形象升华到新的高度,为她的形象平添了厚度和韵味。那茫茫暗夜里的小桔灯,不恰是对小姑娘的绝好象征吗?
其五,《小桔灯》之美,美在运用了相互衬托、交相辉映的表现手法。首先,小姑娘的言行是通过“我”的观察表现出来的,而“我”的感受也伴随着对小姑娘的描写而逐步流露,“我”的感情也伴随着对她的了解而不断升华,由初遇的“同情”,到了解后的“可爱”,直到最后告别时的“敬佩”。“我”的感受有力地衬托了主人公形象的可爱,心灵的美好、高尚。其次,作者着意描绘了小姑娘特定的生活处境,对她的内心世界也是有力的衬托。正是在她的生活逆境和磨难中,她那美好的内心世界才越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其三,用自然景物来衬托小桔灯:阴沉、迷茫、黑暗的自然环境,与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相一致,而小桔灯那微弱的红光,却给人们带来活力和生机。这一衬托显示了小桔灯的象征意义,使主题更加鲜明。这种多角度的衬托手法的运用,增添了文章的立体感,也更加强了主人公形象的美的魅力。
这篇文章记述了“我”在重庆郊外一次访友过程中意外结识一位小姑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怀。文章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春节前夕的重庆,是一个和当时重庆环境、气候同样阴沉黑暗的下午到黑夜一件偶然遇到的事,小桔灯是黑暗社会里光明的象征,是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精神的写照。这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广大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灾难深重,渴望光明。作者以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必将被消灭,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必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