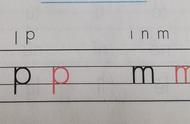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莫欧礼:中国通过科举任用官僚,是中国政治和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即使在唐代科举诞生初期,它也是一个会淘汰大部分考生的制度。这样一个制度注定会激发怨恨和嫉妒,但同时会促进对国家的忠诚。一个制度如果能让大多数参与者反复失败,且同时能增进忠诚意识,那它不啻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治理手段。
几方面的原因强化了这个制度。首先,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上层贵族都想建立一套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与教化、改良和文学有关的价值,这些都可以用“文”这个核心词加以浓缩概括。科举仪式成为这些理想价值的一种外化表演。我们通常觉得唐代文化是开放的和国际化的,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它也是高度保守和怀旧的。许多著名唐代政治理想阐说对汉代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推崇,常把唐代的法制、礼制、学术体制、官僚体制与汉代甚至周代进行对比。考虑到这样的对比常常用来革新机构和政府制度,这种保守主义其实具有创造性。尽管这些阐说不一定没有分歧,它们仍可以仰仗一个共同的传统,我之前称之为“大传统”。参加科举仪式的人会想象他们参加的活动是与过去有关联的,这使他们当下的政治活动获得合法性。他们就同一个题目撰写考试答案,他们的价值,以及他们实践仪式的行动本身,都逐步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可见的部分,这种公共文化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接下来的时代仍持续存在。
宋代以降,科举的规模逐步扩大,科举仪式的社会和政治意涵随之产生变化。失利者的队伍扩大了,乃至时而有*乱的举子放火烧掉衙门。然而这套制度延续了下来。精英治国的理想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关键,当然,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但包括科举仪式在内的众多文化活动仍维系着这种理想。国家、个人、家族都从科举获利。试想有多少新科举子及第后缔结了新的婚姻?科举调节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每个地方社会都有当地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名门望族。科举在民族学上的重要性更显示出它多文化融合的特点。有多少穆斯林学者参加了明代科举并获得成功?这种民族和宗教融入在唐代就有先例,一些韩国士子参加了唐代科举考试,甚至有说法(尽管可信度不高)说一位波斯举子也参加过。
一个有待更充分研究的方向是科举文化的通俗表现。从明代开始,科举遍及物质文化生产的诸多方面,比如刺绣、铜镜和瓷碗等,上面经常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这样的吉利话。赌博游戏也从科举中汲取灵感,我在中国的集市上买到过状元筹、升官图等游戏。市场上肯定有很多假货,即便如此,这些游戏都是很有趣的现象,它们显示出人们一度关心的是什么。中国早期的报纸,如《申报》《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白话画图日报》等,都刊登引人入胜的科举速报。举个例子,《湘报》刊登了一则新闻,1891年在广州的考场上抓住了两名枪替,事后他们的照片被贴在文场(考试院)里示众。这是个很特殊的例子,把我过去和现在的研究兴趣都勾连起来了。
唐代科举取士的仪式重心由官方逐渐转向私人,我或许过分夸大了这种转变,但我仍认为考官和举子的个人作用是逐渐加强的。有些私人的小型仪式或许早有雏形,只是没有人注意,而应试人参加的国家组织的大型仪式(比如“朝见”)则研究多多。初唐经历了一个快速中央集权化过程,但唐代在前150年里推进中央集权尚且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整个300年的时间跨度了。随着中央的权力衰落,老牌学者和政治家开始越发倚靠自己的资源,他们在公开和私下都有密切往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察觉到自己对重建官僚精英群体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这是科举体制最不可思议的一面:那些为国家取士制度效劳的人,能把持这个制度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可以为自己谋取社会和政治利益。
从较长时间段来看,科举仪式空间大小的变化导致其重要性起起落落。开封比长安小得多,什么仪式场所能容纳上千名乡贡就成为一大挑战。宋代的仪式规模普遍较小,这一点能具象地看出来。比如,比较唐宋帝陵的话,河南的宋帝陵比西安北边的关中唐十八陵占地面积要小得多。宋代的政府仪式大幅削减,而唐代常以这方面的巨额开支著称。此后又为之一变,金、元、明、清的政治家们热衷于回望唐代,这些朝代都城规模不断增大,为政府体系不断增员提供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