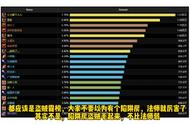在西安西面110千米的扶风县内,耸立着一座佛教舍利塔——法门寺寺塔。该塔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在佛教当中,佛塔是保藏舍利的标志,法门寺因舍利而建塔,因塔而建寺,法门寺寺塔就是一座佛教舍利塔。
二十几年前,全国各地在修复重大古迹时总要立碑为纪。但是,碑文请谁来写,成了一个难题。不少地方向当地文化界和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多数投给了余秋雨。大家充分信任他的阐述高度、文字魅力和文化声誉。余秋雨写成碑文后,接下来应该选择书法家来抄写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陕西虽然为书画大省,书法高手也是不少,但是余先生自己的书法也非常出色,于是就出现了碑文、碑书皆出一人之手的美事。这在现代,已不可多见。
余秋雨为法门寺所写的碑文,受到各地专家的高度评价。他的碑文,突破老式碑文的骈赋套路,恢宏、高雅、畅达,具有现代思维高度,又便于普通游人诵读;他的碑书,吸取二王、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的行书风姿,兼容庄严和潇洒。


法门寺碑
缘起佛指在此,指点苍茫。遥想当初,隐然潜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
渺渺千年,再见天光,众生惊悦,世运已畅。觉者顿悟,兴衰巨掌。
法门于斯,吐纳无量。矫矫魏晋,赫赫盛唐。袈裟飘忽,驼影浩荡。
梵呗如云,诗韵如浪。祈愿此门,不再雕敝。启迪人间,引渡万方。
三十年前,山河重醒。山河之醒,先醒人颜,复醒道路,三醒古迹。人颜之醒,醒其生机;道路之醒,醒其脉力;古迹之醒,醒其尊严。
忆其时也,九州大地,由躁而静,由浮而定,由浪而敬。阡陌之间,渐有人群访故寻迹,补残修颓。若见古碑,则分外尊崇。抚石如抚先祖,辨文如领遗训。抚毕辨罢,起身而立,拭泪远视,决意立新碑于古墟,续题额于当代,接文脉于将断,呼史魂于未溃。
然而,新碑由谁为文,由谁书写?如此难题,不易定夺,遂请各地报刊,调查民意。岂料当时民意,多归一人。此人何人?即在下也。于今回想,余犹深感汗颜,愧不敢当。
中国历来依仰官衔,而余无官无衔,纯一布衣,竟获各地同选,诚为古今罕事。
退而言之,民众选余为文,尚有依稀理由,却又何以知余能书?莫非天有隐眼,监察多年,见余自少习书,晨窗夜灯,长而问帖,拜王谒颜?
天意安排,无因无由。大凡无因无由之命,万万不可推却。此事更涉山河之托,尤其庄重无比。余唯默受之,怯承之,深感之,静悟之。于是沐手焚香,恭而执笔。点划如杵,轻叩吾心,墨色如云,尽倾吾情。先后计有仰韶遗址、炎帝陵、秦长城、都江堰、云冈、法门寺、采石矶、大圣塔、金佛山、峨眉讲堂、五磊寺,兼有胜景题额,如玉龙雪山、昆仑第一城、乌江大桥等等。书罢卷之,分寄各地,如放群鹤,身心俱驰。

遥想山麓水侧,古磐老藤,刻凿之声,昼夜不息。镌入岩壁,锲进历史,叮当似乐,合成恢宏。千年在手,万里在怀,余生何幸,膺此荣命。
当时尚无复印存稿之技,故而所寄墨迹,皆已耗于刻凿。此番收集,皆为重写,文句亦有改动。
除上述大碑外,余之笔墨,更多抄写经籍。所抄经籍,亦常受邀各地,付之镌刻,如受邀佛教胜地普陀山、宝华山抄写《心经》而付之石刻,受邀道教胜地茅山抄写《逍遥游》而付之石刻。抄写既久,便发心今译,以便今日民众畅快领悟。余之今译,集学术之惠,戒学术之弊,求清通流丽,探千古诗魂。今译之中,面对屈原最为用功,面对苏轼最为惬意。今译之后,又奉献长篇论述,多方阐释经籍,由此组成书法、今译、论述之三相结构。
至此余心甚慰,余意已足。回首往昔,如许经籍,教余为人,助余立世,定余格局,铸余心魄。余自幼诵之、背之、含之、品之,今则温之、书之、译之、论之。毕生文事,莫此为要。值此霜鬓时节,理当公之诸友。望诸友读罢译论,再返书法。看吾笔吾墨,撇捺提顿,皆是赤诚意绪,醮泪游动。
本书于选印大碑和经典之余,又加入自己平日所写之部分诗词,及赠送友人之书法作品,让读者于庄严之后,略感轻松。
编罢两集,纸积如堆。笑余毕生长途,步步不离墨迹。谨以五言小句,略述日常生态。藏头“秋雨笔墨”,以结此文——
秋窗写大碑,雨夜抄经籍,笔丰藏远山,墨浅唤吾妻。
余秋雨作序于甲午初夏,修改于乙未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