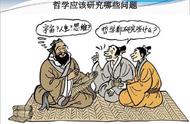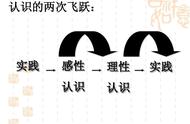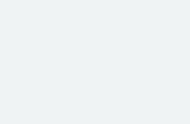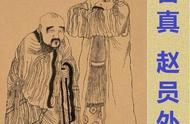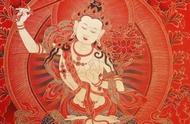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念的性质和范围。它的权限还包括为我们不了解各种知识的怀疑结论制定和评估论据。此外,认识论者讨论与这些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的主题,包括对思维过程的评估以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下是认识论当代发展的概述。
知识分析对知识的传统分析是,它是三个条件的组合:真理、信念和理由。这个想法是,对于拥有事实知识的人来说,所知道的必须是事实,因此是真实的;该人必须认为它是真实的,即相信它;并且该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也就是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这些条件产生的知识被定义为一个充分证明的真实信念。
Edmund Gettier (1963) 发表的一篇关于传统分析的简短批判性讨论引发了认识论的一系列活动。盖蒂尔通过提供令人信服的反例驳斥了传统的分析。他描述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某人基于强有力的证据形成了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只是由于幸运的意外而发生的,与证据无关。这是一个类似于 Gettier 的示例。有人在附近的田野里看到了看起来非常像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该人有理由相信田间有一只羊。事实证明,这个人看到的不是一只羊。这是一个高度逼真的雕像。然而,这个人' 相信田野里有一只羊是正确的,因为幸运的巧合是在田野的其他地方隐藏着一只真正的羊。这种信念显然不是知识的一个例子,尽管它是一个被证实的真实信念的例子。因此,有正当理由的真实信念对于知识来说是不够的。
论证例子中的人没有足够的基础相信田野里有一只羊似乎需要采取一般立场,即很少有信念是合理的。因为如果那个人没有足够的依据并且没有正当理由,那么在类似情况下确实看到一只羊的人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她的视觉信息不会更好。在几乎所有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尽管不寻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基于可比较的原因具有相同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只是在这种偶然的方式下才是正确的。因此,通过提高辩护标准来回应盖蒂尔案会导致我们知之甚少的结论。
大多数认识论者对盖蒂尔的例子做出了回应,除了寻求正当的真实信念之外,还寻求知识的第四个条件。有人提出,要拥有知识,还要求一个人的信仰的正当性是不败的,这大致意味着没有真理会破坏信仰的正当性(Klein 1976)。其他人建议,在知识的情况下,证明不涉及虚假(Chisholm 1989)。还有一些人要求证明一个已知信念的理由是决定性的 ——粗略地说,除非信念为真,否则不会存在的原因(Dretske 1971)。反例驳斥了这些分析的原始版本,更复杂的分析取代了原始版本,随后出现了新的反例。(请参阅 Shope [1983] 以获取对 Gettier 示例的响应的详细摘要。)
并非所有认识论者都接受知识的三个传统条件的必要性。有些人拒绝理由条件。一个提议的替代方案要求已知信念与使该信念为真的事实之间存在适当的因果关系(Armstrong 1973,Goldman 1967)。另一个提议的替代方案要求一个已知的信念与该信念的真实性相反地变化:如果该信念不真实,则不会以相同的方法相信它,如果它为真,则会以相同的方法相信它(诺齐克1981)。其他人则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否认可以提供任何必要和充分条件的知识。知识的另一种解释是它是最具包容性的事实精神状态(威廉姆森 2000)。如果精神状态的存在保证其真实性,则该精神状态是事实性的。与传统的分析不同,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知识的概念可以分解成部分。
尽管认识论者从这项研究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对于像盖蒂尔这样的例子所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达成共识。
理由: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在 Gettier 问题之后,对正当性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正当性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无限回归问题。通常,一个信念是合理的,因为它得到了其他信念的支持。例如,根据艾伦、芭芭拉和卡罗尔在隔壁房间的合理信念推断,某人可能有理由相信隔壁房间有人。支持性信念获得了其他信念的支持。艾伦、芭芭拉和卡罗尔在隔壁房间的信念可能是通过从他们说他们会进入隔壁房间然后大喊他们已经这样做的合理信念推断出来的。然而,鉴于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证明信念是不可能无限倒退的。因此,要么有一些信念——基本信念——在没有其他信念支持的情况下是合理的;或者我们的信念形成某种圈子或网络,每个合理/合理的信念都得到系统内其他信念的支持;或者我们的信仰根本没有道理。基础主义支持第一种选择,而连贯主义支持第二种选择。第三种选择,即没有任何信仰有任何理由,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经典的基础主义观点是,只要一个信念是基本信念或建立在基本信念的基础上,它就是合理的。通常,基本信念的内容被认为是关于信徒心理状态的命题。例如,当某人在良好的观看条件下观察一个普通的物理对象时,该人的视觉系统就会产生一种体验状态。这是观察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可以通过内省得知。相信自己处于这种体验状态被认为是一种基本信念。这种信念应该为我们其他正当的信念提供安全的基础。经典的基础主义者对基本信念的安全性来源持不同意见。候选来源包括我们内省能力的所谓无误性以及对某些信念的怀疑免于怀疑。根据经典的基础主义,我们通过从我们对自己状态的内省证明的信念中进行推理,获得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证明信念。一些基础主义者认为,只有演绎的(逻辑上必要的)联系才能为知识提供充分的理由,而其他人则认为归纳或解释关系也足够了。什么支持对知识足够强大的问题是认识论怀疑论讨论的核心。通过从我们内省的关于我们自己状态的正当信念中进行推断,我们获得了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正当信念。一些基础主义者认为,只有演绎的(逻辑上必要的)联系才能为知识提供充分的理由,而其他人则认为归纳或解释关系也足够了。什么支持对知识足够强大的问题是认识论怀疑论讨论的核心。通过从我们内省的关于我们自己状态的正当信念中进行推断,我们获得了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正当信念。一些基础主义者认为,只有演绎的(逻辑上必要的)联系才能为知识提供充分的理由,而其他人则认为归纳或解释关系也足够了。什么支持对知识足够强大的问题是认识论怀疑论讨论的核心。
一些基础主义者放宽了对基本信仰的要求(Chisholm 1989,Huemer 2001)。基础主义的中心观点是,每个被证明的信念都是基本的,或者从基本信念中推导出它的证明。这种观点并不要求基本信念是确定的或无误的。更适度的独立支持足以阻止派生论证的倒退。基础主义者可以始终如一地认为,来自其他信仰的支持使基本信仰超出了这个适度的水平。如果基本信念不需要最大程度地安全,那么与经典观点的另一种背离就会变得有吸引力。基本信念可以包括普通的知觉信念。例如,人们看到一只狗的信念可能是基本的。它可以直接从经验中获得一些独立于其他信念的理由,这在视觉上就像一个人在看一只狗。温和的基础主义被广泛认为是对古典基础主义的改进。
然而,温和的基础主义也有一些批评者。它的捍卫者被要求解释基本信念如何从经验中得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支持(BonJour 1985)。主要问题是,最容易理解的认识论支持是由强有力的论证的前提为其结论提供的理由,但温和的基础主义者引用的提供基础支持的经验似乎并不符合论证的前提。这是因为经验不是陈述,但唯一可以作为前提的事物是陈述。
连贯主义是基础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Lehrer 1974,BonJour 1985)。连贯论者否认存在任何基本信念。根据连贯论者的观点,经典基础论者寻求的安全基础是不可能的。他们争辩说,所有被证明的信念都是从一组信念之间保持的连贯关系中得到证明的。连贯论者试图说明什么构成连贯性,经常诉诸信念之间的解释性关系作为连贯性的来源。一些人提出,正当化源于反思平衡 ——对特定案例的信念和对涵盖这些案例的一般原则的信念的相互调整,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它们之间的解释关系(Goodman 1984)。
连贯主义者一直受到挑战,以避免他们理论的明显暗示,即合理的信念可能与感官输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分离。一组信念可以是内部连贯的,而这些信念没有考虑到人的经历,但连贯性似乎意味着这些连贯的信念是合理的。然而,从直觉上看,这种信念似乎与通过将一些精心制作、精心制作但奇妙的故事中的一切都视为真实而形成的信念一样不合理。
并非所有哲学家都同意我们必须在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一些人认为,双方的核心认识论考虑是可以调和的(Alston 1989,Haack 1993,Sosa 1991)。
理由:其他问题除了制定和评估基础主义、连贯主义和其他证成理论之外,认识论者还解决了有关认识论证成的各种其他问题。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的标准版本都有一个预设,即正当化是由我们思想中可反思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经验状态、信念、记忆、推论等等。然而,一些哲学家反对这种内在主义的预设,引发了对这种关于辩护的观点与其外在主义替代方案之间的对比的广泛讨论。(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请参见 Kornblith 2001。)
对于内在主义者来说,辩护完全由内部心理因素决定,而外在主义者则认为辩护至少部分由其他事物决定。一些内在主义者还要求信徒了解所有称义的因素。一个典型的内在主义理论是证据主义,它认为所持有的证据决定了信念的认知状态(Conee and Feldman 2004, Haack 1993)。可靠性主义体现了外在主义的观点(Goldman 1979)。可靠性主义坚持认为,信念的正当性取决于产生对导致信念的过程或机制的真实信念的倾向。这种可靠性不是内部因素,因为信念的真实性通常不是内部事实。
一个很好的例子来指出内在主义理论和可靠主义之间的区别,涉及到一个欺骗性恶魔的受害者。恶魔通过对普通环境的感知,诱使受害者拥有理性人可能拥有的体验。恶魔的受害者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同的外部世界信念。这个例子的另一个部分是恶魔受害者的外部世界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环境,因此她对外部世界的信念是不正确的。在这样的例子中,导致受害者的外部世界信念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产生了她完全错误的外部世界信念。因此,可靠性主义似乎暗示这种信念是不合理的。假设对方在正常环境中的信念形成过程是可靠的,因此可靠性主义意味着此人的信念是合理的。相比之下,根据任何内在主义理论,如果个体处于相同的内在状态,则正常情况下的人和恶魔受害者的信念同样有充分的理由。
自推出以来,可靠性主义一直是严格审查的主题。批评者认为,可靠性论者无法合理地说明理论所依赖的信念形成过程或机制的类型(Conee and Feldman 2004)。例如,形成典型的视觉信念的过程可以无限地分类为感知、视觉感知、放松时的信念获得、非推断的信念获得等。问题是指定这些过程类型中的哪一个必须是可靠的,以便为由此产生的信念进行辩护。可靠性主义者必须为所有导致正当信念的过程指定相关类型。
一些正当性理论需要对可靠性进行补充。例如,一个适当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当一个信念是由一个在适当环境中正常运作的普遍可靠的认知系统的运作产生时,该信念是合理的。这种观点的一个有神论变体认为,人类认知系统的正常功能是创造者意图的结果(Plantinga 1993)。在无神论的版本中,适当的功能是由自然选择力决定的。对正确功能主义方法的一个突出批评是,认知机制有可能不正确但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感知机制可能会意外地工作得比设计的要好得多。由此产生的信念可以通过敏锐的感知得到特别好的证明。
认识论者还比较了认识论的正当性和诸如义务之类的伦理概念。讨论一个人相信什么是合理的很容易滑入讨论这个人应该相信什么或有权相信什么相信。这种谈话至少在表面上类似于对一个人应该如何行为以及该人有权做什么的道德评价。似乎认知评估和伦理评估在根本上是相同的。然而,关于伦理评估对信仰的适用性存在一些问题。人们普遍认为,道德上应该做的事情仅限于他可以做的事情。如果认识论中有类似的东西,那么人们应该相信的仅限于那些可以相信的事情。显然,从这个前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有理由拥有信仰,信仰就必须在我们的自愿控制之下。然而,信仰似乎通常不受自愿控制。一些哲学家的回应是,与表面现象相反,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有足够的控制权;一些人争辩说,即使我们无法控制是否相信某些命题,但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命题是可以接受的;和其他人得出的结论是,很少(如果有的话)信念是合理的,因为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也有人担心信仰的认知证明与信仰的道德或实践利益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收集在 Steup 2001 中。)也有人担心信仰的认知证明与信仰的道德或实践利益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收集在 Steup 2001 中。)也有人担心信仰的认知证明与信仰的道德或实践利益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收集在 Steup 2001 中。)
另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先验证明和后验证明之间的区别。当一个信念不是从经验中得出时,它的证成是先天的,而当它来自经验时,证成是后天的。先验证明和知识的主要候选人是对数学和逻辑基本真理的信念。其他候选者包括显然完全由概念关系实现的信念,例如任何红色都是有颜色的信念。这些据称是先验证明的命题,如果为真,则必然为真。
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先验证明似乎是神秘的,因为很难理解什么可以独立于经验来证明信念。关于信念如何具有先验的理由,已经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在自然主义的方法中,先验的证明来自于保证真理和证明的信念形成过程的运作(Kitcher 1980)。模态可靠性方法认为,概念直觉必然向我们展示大部分真理(Bealer 2000)。一种坚决的传统方法认为,人类具有理性洞察力的能力,可以在某些思想中找到真理和必要联系(BonJour 1998)。
似乎一个信念不可能是先验的或已知的,除非它的真实性以某种方式被抽象地保证。看来,如果有一个信念是真实的抽象保证,那么该信念的真实性绝不能只是偶然的。因此,对偶然真理的先验知识将是令人惊讶的。然而,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知识(Kripke 1980),并提出以下论点:假设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间谍;对此一无所知并且完全在我们的扶手椅上进行推理,我们可以规定“Stretch”这个名字指的是碰巧是最高间谍的人,如果有的话。这样做之后,似乎我们可以从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从逻辑上推断出,从而先验地知道以下偶然事实:如果有一个独特的最高间谍,那么Stretch就是一个间谍。也许这种知识不是严格的先验知识,因为我们将使用我们引入“Stretch”这个名字的经验。尽管如此,它似乎是一种了解至少与先验知识非常相似的偶然真理的方法。
怀疑论许多传统的怀疑论点诉诸错误的可能性。怀疑论者经常指出,即使我们对外部世界最自信的信念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欺骗性恶魔或其他欺骗来源的影响。怀疑论者通常会进一步声称,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甚至对我们最有信心相信的世界事物都缺乏了解。(在 DeRose 1999 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怀疑主义的有影响力的论文。)
易错论是对怀疑论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反应的核心(Chisholm 1989,Pryor 2000)。易错论是一种观点,即知识与基于相同基础的相同信念是错误的可能性相容。例如,有人清楚地看到前院有一棵树,并在正常的感知基础上相信前院有一棵树,这可能会导致某种错误。视觉上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样的体验可能是由于欺骗性恶魔的努力而产生的。然而,一个典型的人看到一棵树完全没有理由认为任何这种奇怪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真的有一棵树存在。易错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有足够的理由知道院子里有一棵树。根据易错论者的说法,像关于错误可能性的怀疑论点依赖于将知识的正当性标准设置得太高。我们可以拥有知识,即使我们不能像怀疑论者错误地将知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绝对免于错误。
易错论并非没有问题。要解释我们的经验证据是什么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是在普通物体面前而不是某种欺骗的受害者,这并非易事。一些认识论者争辩说,我们对外部世界信念的证明取决于对我们经验的最佳解释的推论(Vogel 1990),而其他人则争辩说,经验的特征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使它们指示外部世界对象。充分阐明为什么我们的信念甚至是错误的理由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
一些有影响力的怀疑论论据是基于被梦或恶魔欺骗的可能性的论据的更新版本。较新的论点常常诉诸于成为缸中之脑的可能性。缸中脑的论证利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功能齐全的人脑,浸入一个维持生命的化学物质缸中,接收计算机控制的神经刺激,与普通人在普通人身上的神经刺激完全匹配。环境。缸中脑论证的前提是,就我们所知,我们中的任何人实际上都可能是缸中脑。该论证还假设,由于这种可能性可能是真实的,我们缺乏对真实外部世界的了解。
对这些论点的一个讨论较多的答复采用了因果参考观点(Putnam)。在一种解释中,答复以令人惊讶的论点开始,即被困在缸中的大脑所表达的“我是缸中的大脑”将是错误的。一个终生被困在桶中的大脑会从一些计算机生成的刺激中学到“桶”这个词。计算机中刺激的起源与大脑的容器没有因果关系,而大脑的术语vat需要应用于容器。因此,根据因果关系参考,大脑的句子我是缸中的大脑不会是真的。当然,正常情况下的人用同一句话表达的也是假的。因此,无论我们实际处于这些情况中的哪一种,我是缸中的大脑这句话都没有表达真理。反怀疑论的答复得出结论,通过使用因果关系观点,我们可以证明否认大脑中的存在是合理的。 a-vat 论证的前提是,就我们所知,我们可能是缸中之脑。
这种反怀疑的回答是否成功是有争议的。无论如何,该方法的一个显着限制是它最多驳斥了仅依赖于一些缸中之脑的可能性的怀疑论点。例如,一种不受回复影响的可能性是我们最近变成了缸中的大脑,我们的术语缸是指包含我们的缸,因为在我们缸前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适当的因果关系。
怀疑论点经常依赖于认知闭包原则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一个命题并看到紧随其后的另一个命题,那么这个人也知道后一个命题。如果有人知道一个普通的事实,例如她正在看一张桌子,那么封闭原理意味着她可以通过演绎知道她不仅仅是缸中之脑。因为,根据一些怀疑论者,她无法知道她不是缸中之脑,所以怀疑论者得出结论,她不知道可以从中推断出这一点的任何事情,例如她正在看一张桌子。一些哲学家否认封闭原则,试图反对这种对普通事实知识持怀疑态度的案例。然而,大多数哲学家争辩说,闭包原则的某些版本一定是正确的,怀疑论者的任何错误
对怀疑论的另一种回应诉诸认知语境主义(Cohen 1999,Lewis 1996)。情境主义者努力解释怀疑论论据的直觉吸引力,同时允许我们对知识的许多普通归因是正确的。他们的中心论点是关于句子使用的真值条件,包括单词know和 kindred 术语。语句的特定用法的真值条件陈述指定了为了使该语句的该用法陈述真值而必须实现的条件。认知语境主义的主要形式认为,任何句子的特定用法的真值条件包括知道,或同源表达式,随句子使用的上下文而变化。
通常,真值条件的变化方面被称为知识位置的强度,这是句子主语使用知道应用于主题。通常,语境主义者断言,认知位置所需的强度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在其低端允许许多将“知识”归因于某人的真实句子。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将基于感知、记忆、证词以及归纳概括和对最佳解释的推理的信念归类为“知识”信念时,我们所说的通常是正确的。情境主义者通常还断言,某些情境在变异范围的高端,要求足以真正否认外部世界的“知识”。例如,情境主义者经常声称,在怀疑主义问题突出的地方,“知识”真正归属的标准非常高,因此,
一些语境主义的批评者否认怀疑主义是正确的,即使它的论据很突出。批评者诉诸于诸如上述讨论的易谬论之类的反怀疑论理由,认为这些论点都失败了,无论我们是否考虑,怀疑论都是错误的(Conee and Feldman 2004)。其他批评者质疑语境主义的语言基础(Stanley 2004)。
背离传统对知识、辩护和怀疑的哲学研究是传统认识论的核心。一些认识论者扩展了这门学科。一个这样的扩展涉及将认识论与关于人们如何形成信念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信息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大致认为,认识论与研究人类认知的科学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一些哲学家支持自然主义,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在关于认知的科学/经验问题与认识论核心的概念问题之间找到了相当明确的区别。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主张放弃传统认识论,并用最接近的经验学科认知心理学取而代之(奎因 1969)。很少有哲学家为这种极端观点辩护。然而,许多人敦促认识论与人类认知的实证研究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例如,强调寻找改进推理方法的认识论者认为,对人们实际推理方式的实证研究对于制定有用的建议至关重要(Kornblith 1994)。相信认识论的主要作用是解释知识、证明等概念的哲学家通常认为经验输入的空间较小。一些人提倡一种不那么极端的自然化认识论形式,它需要用他们认为在自然主义上合法的术语来解释中心认识论概念。
传统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强调关于知识和证明的问题,因为它们适用于个人。然而,出现了一种社会认识论,它提出了以下问题:群体拥有知识是什么以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知识的传播和发展(Schmitt 1994,Goldman 1999)。
认识论中的另一种方法强调了认识论的美德(Sosa 1991)。美德认识论的一个版本是前面讨论的可靠主义观点的变体。这种方法试图根据产生可靠真实信念的认知美德来表征知识或证明,例如思想开放和愿意考虑新证据。与传统问题更大的背离,其他版本的美德认识论提出,认识论者用美德认识论行为取代或补充传统主题。
认识论及相关学科关于心灵哲学中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广泛而重要的认识论工作。心灵哲学中的外在主义,通常称为内容外在主义,是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即环境因素可以帮助确定某些心理状态的身份。一个简单的内容外在主义主张是,一个人的思想内容用自然种类的术语表述,例如榆树和水, 取决于与该人学习该术语实际涉及的种类的因果关系。如果这种联系与不同的自然种类有关,那么用相同的术语表述的人的思想就会包含一个概念,而不是指代另一种。不需要有任何显着特征向人显示该人的想法是关于哪种类型的。
表面上看,如果这个简单的内容外在主义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先验地知道它。我们可以知道,外因有助于确定一些思想内容,只要考虑我们的自然类术语的指称如何在一些因果不同的假设情况下直观地变化。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该理论似乎与两个似是而非的认识论学说的结合不相容。其中一个教义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自己思想的内省关注来了解它们的内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将我们对简单内容外在主义理论的先验知识与我们对可以用水表达的一种思想内容的内省知识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推断水与思想有因果关系,因此水存在。然而,根据第二个似是而非的认识论学说,了解我们的环境并不那么容易。它需要经验信息。因此,简单的内容外在主义理论似乎暗示,要么我们无法像其他方式那样容易地了解我们思想的内容,要么我们环境中事物存在的经验知识比其他方式看起来更容易。
对这种推理方式的批评者询问是否真的可以在没有实证调查的情况下知道内容外在主义适用于我们的任何概念。此处描述的内容外在主义版本对概念的适用性取决于概念与某种自然类型之间是否存在适当的因果关系。这种依赖性表明,需要关于存在正确连接类型的经验信息来证明将内容外在主义应用于我们的概念是合理的。(有关进一步讨论,请参阅 Nuccetelli 2003 中的文章。)
在哲学的其他领域已经完成了许多符合认识论的条件。下面是对相关领域的一些认识论工作的简要清单。一个经典的认识论主题是归纳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即确定人们是否可以使用对某些案例的观察来对未观察到的案例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可以做到,请解释此类推论何时以及为什么是合理的。这个问题一直在被称为确认理论的科学哲学部分中进行。第二,事实性知识包含真理。真理是认识论中的一个传统话题。在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和哲学逻辑中也提出和讨论了各种真理理论。第三,信念的理性改变与正当信念的认识论主题密切相关。理性信念变化是概率论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贝叶斯认识论的分类下。第四,认识论问题往往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很重要。与道德有关的认知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道德正确的问题,通常在主要关于道德哲学的作品中讨论。同样,与上帝有关的认识论问题主要在宗教哲学著作中讨论。最后,在认识论和认知科学之间的边界附近,人们对所谓的知识来源的性质以及它们进行认知工作的方式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
认识论术语认识论是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使用两个独立的含义。在英语国家,认识论泛指知识的哲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包括诸如有效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这种有效性的性质分析、知识的基础知识等主题和问题。推理或经验和感官,对不同类型知识的分析,以及知识的局限性。在欧洲大陆,上述问题被认为是更一般的学科领域的一部分,认识论(gnoséologie在法国,gnoseologia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或知识论(Erkenntnistheorie(德语),而认识论探究的目的仅限于科学知识。
在这第二种意义上,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基本认识论问题变成了:“是否有可能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现实的任何有效知识?如果有,通过什么方式?” 正如这些问题所表明的,认识论问题不可避免地与方法论问题相互关联。然而,它们不能被简化为简单的技术程序及其有效性,正如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试图做的那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意识至少应该处理四个主要问题:
- 社会科学对象(即社会现实)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对象(即自然现实)的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吗?
- 因此,研究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最合适的 gnoseological 程序是什么?
- 我们确定通过研究特定的社会现实获得的特定知识可以概括吗?
-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假设社会事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从历史上看,各种社会学传统或学派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我们将通过追踪发生在三对对立的社会学和认识论思想流派之间的三个主要认识论辩论来追溯它们: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辩证理论、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在 19 世纪初,社会学学科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实证科学,并反对关于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思辨。根据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说法,这意味着将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科学方法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他的社会物理学(Comte 1830-42)是工业革命新文化的表现以及其完全计划好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抱负。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是有机的和进步的,并且天真地相信将社会规律的科学知识自动转化为新的和谐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孔德关于科学方法的可靠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不加批判的假设至少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部分缓和,他认为孔德的思想是不自由的和教条主义的,即一旦社会学规律通过自然科学的相同科学方法建立,它们就可以不再被质疑。密尔反对科学知识永远不能提供绝对的确定性,他在他的逻辑、推理和归纳系统(1834 年)中有机地确立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从大卫·休谟的认识论立场出发, Mill 认为知识从根本上基于人类经验,归纳是其适当的方法。归纳概括的可能性是基于人性的规律性和统一性的思想,由规律来协调;甚至社会事件也以经验法则的形式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主观性的形式逻辑结构。
英国实证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在赫伯特·斯宾塞身上尤为明显,他反对孔德的社会有机主义观点,即特定相对于有机整体的更大重要性。他对进化概念的核心关注为他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视角来研究整个现实,使用生物进化和无机进化的类比来考虑社会进化(1876-1896)。然而,社会学思想中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最完整发展当然包含在埃米尔·涂尔*著作Les régles de la méthode sociallogique (1895) 中。他所说的faits sociaux(社会事实)可以根据四个标准来表征:其中两个标准与所观察的对象有关,而另外两个标准与观察它们的社会学家有关。
第一个标准将社会事实视为个人良心之外的现实:社会制度具有独立于个人生活的生活。第二个标准是,社会事实的这种外在的、客观的性质因此赋予它们对个人的规范的、强制性的权力:这些社会事实强加给他,即使没有他的意愿。道德、舆论、法律、习俗都是这样的例子。社会事实的这两个特征要求观察它们的社会科学家遵守另外两个限定标准。首先,它们应该被视为“事物”,即它们应该作为一种外部的、客观的现实来研究,与个体意识相分离。其次,符合他们的本性,社会事实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因果关系的本质是特定的,既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原因,也不能归结为生物学因果关系,正如斯宾塞的进化论所暗示的那样。从心理和生物现象的层面上,社会现象的新兴本质奠定了它们自主、独特的现实基础: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应该采用因果关系的单线概念:相同的结果总是对应相同的原因。根据涂尔*说法,任何多重原因都涉及不可能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原则进行分类。既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原因,也不能归结为生物学因果关系,正如斯宾塞的进化论所暗示的那样。从心理和生物现象的层面上,社会现象的新兴本质奠定了它们自主、独特的现实基础: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应该采用因果关系的单线概念:相同的结果总是对应相同的原因。根据涂尔*说法,任何多重原因都涉及不可能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原则进行分类。既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原因,也不能归结为生物学因果关系,正如斯宾塞的进化论所暗示的那样。从心理和生物现象的层面上,社会现象的新兴本质奠定了它们自主、独特的现实基础: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应该采用因果关系的单线概念:相同的结果总是对应相同的原因。根据涂尔*说法,任何多重原因都涉及不可能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原则进行分类。独特的现实: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应该采用因果关系的单线概念:相同的结果总是对应相同的原因。根据涂尔*说法,任何多重原因都涉及不可能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原则进行分类。独特的现实:这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应该采用因果关系的单线概念:相同的结果总是对应相同的原因。根据涂尔*说法,任何多重原因都涉及不可能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原则进行分类。
总之,我们可以说社会学的经典实证主义范式的特点是承认社会事实的特殊性质是从现实的其他领域出现的。然而,这意味着将社会学视为一门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使用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得成功的相同方法(方法论一元论),并以感官所感知的经验为基础,并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归纳)。最后,对社会事实的正确解释应该只考虑每个结果的一个原因(单一因果决定论)。
对这种社会学认识论观点的严峻挑战来自德国历史学派:19 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德国发生的关于方法(methodenstreit)的争论是社会学史上认识论争论的第一个例子。它始于德国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威廉·狄尔泰,他反对孔德和密尔将物理学方法引入“道德科学”的提议。他所谓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与自然科学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因此它们不能共享相同的方法 (Dilthey 1833)。事实上,他们的对象是心理状态,只有通过“移情理解”才能理解的精神体验(Verstehen):“我们解释自然,我们了解精神生活”(同上)。在狄尔泰思想的第一阶段,精神科学的社会历史本质所基于的这种理解不被认为是由感官知觉介导的,而是通过熟人产生直接和直接的直觉知识。然而,在他思想的第二阶段(1905 年),他认为精神生活不是立即可以理解的,而是需要对其在文化生活中的客观表现进行解释学解释。无论如何,他在自然科学的目标(通过外部感官解释erklären数据)和人文科学的范围(理解verstehen通过内心体验)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长期的区别。
Wizhelm Windelband 和 Heinrich Rickert 是德国历史主义的另外两位拥护者,他们批评狄尔泰对自然和精神以及相关科学的区分,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知识始终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不考虑其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根据所使用的形式和不同类型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区别:具体方法是对单一事件的描述,而规范方法则涉及对规律和一般规律的探究(Windelband 1894)。第一种类型的程序是特定科学的典型——尽管不是排他性的——,作为历史的文化科学,必须解释和理解历史事件的个体特征;第二种方法是更典型的一般科学,即旨在建立一般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总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一个异质的连续体(eterogenes Kontinuum);知识可以通过制作一个同质的Kontinuum 来进行,就像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或者通过将异质的Diskretum的一部分分段,比如文化科学所做的。Rickert (1896) 进一步发展了将价值观作为社会历史知识基础的必要性: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 不仅仅是个别学科,如果他们想了解社会历史事件的实际含义,还应该参考价值相关性( Wertbeziehung )。
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进行了调和这两种对立(理解/解释和具体的/规范)的最重要尝试,他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但对其唯心主义取向持批评态度。在他的方法论论文(1904-17)和随后的作品中,韦伯对社会科学中使用的方法的性质和有效性进行了调查,并为他的解释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提出了一个一般的认识论框架。他特别论证了在调查社会行为时的必要性,1) 诉诸一种解释性理解,它没有被因果解释分开, 2) 在避免价值判断的同时,建立主题的价值相关性( Wertbeziehungen ) 作为其文化重要性和科学相关性的标准,以及 3) 使用理想类型方法保留历史事件的社会和文化独特性。这三点构成了韦伯对德国历史主义认识论原则的主要阐述。
关于第一点,韦伯批评威廉·冯特和乔治·齐美尔(受狄尔泰影响)将社会历史知识简化为心理理解,因为这个立场不能支持客观知识:正确理解社会历史事件需要建立一些因果关系,以测试我们的解释性理解。因此,韦伯将社会学的观点设想为既是概括性的、规范性的又是解释性的、具体的科学,主张解释性理解和因果解释的互补性:也就是说,研究人员的个人理解应该与科学解释的实证和统计建立的规律相平衡。 (1913)。
其次,韦伯区分了基于个人信仰和信仰的价值判断和基于科学的事实判断。科学知识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研究人员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对相关性的选择——问题和重点的具体选择。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非评估性和客观性的,一旦根据研究人员的个人价值观选择了优先级,研究人员就应该通过测试支持他的假设的经验证据来进行,从而仅表达事实判断。
最后,韦伯使用理想型概念来解释某些独特的历史事件,使用多元因果关系模型:单一事件总是多重历史联系的结果。在无限的事件流中,问题变成了找出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间可能可以解释这种影响的因素的适当模型。这也暗示了因果关系的概率思想,它超越了典型的实证单线性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方法,它是由多元概率 - 因果关系模型构成的。
德国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遗产——其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二元论方法,对基于解释性理解的 gnoseological 模型的偏爱,以及多重因果关系的概率模型——无疑影响了当代 20 世纪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芝加哥学派(帕克与温德尔班德和齐美尔的接触众所周知),更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解释社会学(通过韦伯和齐美尔)和现象学传统社会学(通过舒茨)。它的影响甚至体现在许多社会学家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选择中,如 Pitrim Aliksandrovič Sorokin (1959) 和 Charles Wright Mills (1959)。总之,这些不同的潮流消极地回答了关于仅通过经验数据获得人类社会现实知识的可能性的认识论问题。他们拒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不接受将科学方法直接应用于社会学分析。当研究人员进行实证研究时,他们求助于由研究人员的认识论选择产生的方法论观点:他们倾向于拒绝技术术语和统计量化,优先考虑常识性概念和语言,并转而采取社会行动者的观点研究人员和科学界的意见。这类定性方法也受到微观社会学的青睐——例如符号互动主义、民族方法论、以及不同种类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它们没有直接受到德国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原则的影响。虽然很少明确说明,但他们的认识论基础,默认地指导他们选择社会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大多与解释和现象学社会学的基础一致。
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遵循经验定量方法,并接受从自然科学中借用的科学方法作为适当和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这一主流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在其最重要的代表拉扎斯菲尔德和伦德伯格以及他们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探究的主要研究工具的利用中非常明显。特别是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不情愿直接解决认识论问题,同时更喜欢实际的实证研究,他以他的新实证主义信念(Gallino 1973:27)而闻名,这些信念植根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哲学运动中的数学和心理学背景。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奥地利首都出现了一批新的实证主义者,即所谓的“维也纳圈”,深受数理逻辑先驱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工作影响。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及法国传统主义Pierre Duhem 和 Jules-Henri Poincaré。马赫认为科学不是事实发现,而是与事实相关的活动:它不能声称发现了关于现实的绝对真理,因为它的定律不是绝对的,但充其量只是“可能性的限制”。罗素是数理逻辑的先驱之一,他尝试建立数学的逻辑基础,该基础考虑了两个学科中都存在的必要性元素。这可以看作是思维逻辑结构的基础。最后,Duhem 和 Poincaré 提出了一种科学理论的想法,认为它是人类思维的纯粹假设和常规结构。
在这些前提下,“维也纳圈”的主要代表——莫里茨·施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和奥托·纽拉特——更喜欢逻辑经验主义或新实证主义的标签将自己与经典实证主义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摒弃了感性主义的观点——知识来源于仅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观察和验证。他们拒绝将经验直接观察作为进行假设检验的唯一手段,并将验证视为“原则上的可检验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接受了没有直接经验参照物的理论结构是有意义的。他们在语言逻辑分析的新基础上更新了经验主义:事实上,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诉诸逻辑和经验来证明语言陈述的真假,并且这两种手段都是事实性的,可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然而,逻辑经验主义仍然保留着经典实证主义的一些基本认识论原则,例如只有经验可验证的知识才有意义,科学是基于归纳的累积过程,物理学方法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方法。 (方法论一元论),并且发现自然规律和一般规律是任何科学的基本目标。对Karl Popper的批评是针对大多数这些基础的,并以某种否定主义的方式将它们颠倒过来(Cipolla 1990)。自从他的第一本主要出版物(波普尔 1934 年)以来,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就提出了与新实证主义者的主要假设相反的信条:首先,归纳法是一种从观察单个案例中推断出一般规律的合适方法。他认为,一个案例足以证明归纳是错误的,并且验证总是依赖于观察理论,这些理论通常来自与推导出被测假设基本相同的理论,这使得他们的测试在逻辑上没有结论。波普尔放弃了验证本身的概念,转而支持证伪,并提出了一种假设-演绎法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假设没有通过适当的测试,它肯定会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如果它与数据一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真的。在任何情况下,波普尔都认为,一个理论只是暂时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它始终是一个推测性假设,将来可能会被推翻。通过这种方式,科学知识永远不会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系统,而是始终对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即使波普尔相信方法论一元论——方法的统一理论——这不是绝对的,而是推测性的、批判性的,并且容易被证伪(1963)。
法兰克福学派对方法论一元论的实质性拒绝是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提倡社会学中辩证方法的必要性。它的认识论原则部分源自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和合理化的思想,部分源自受黑格尔影响的年轻马克思1844 年的哲学经济手稿。它还受到两位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施的强烈影响,以及弗洛伊德。辩证认识论意味着:
- 在整体的做法,即考虑以了解各部分,由整体介导的总体的必要性。
- 否认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离,以把握变迁的辩证过程。
- 对社会和启蒙理性的非理性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一种去神秘化的态度,一旦它成为纯粹的工具并脱离其目标,也就是说,当它成为统治人类和社会的纯粹手段时。
1961 年,社会学认识论历史上第二次最重要的辩论发生在蒂宾根,双方之间是西奥多·阿多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最杰出的两位代表)和卡尔·波普尔。和汉斯·阿尔伯特 (Adorno et al. 1969)。后两者的新实证主义认识论遭到前两者的强烈质疑,批评其辩证性,认为是一种与其内容毫无联系、无法理解社会现实的逻辑形式主义。社会学的目标是超越表面现象,通过将社会解释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社会矛盾和冲突。这意味着拒绝实证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拒绝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拒绝测量和量化的社会现实。除了波普尔和阿尔伯特,法兰克福学者的实际目标是美国社会学学派,其实证分析框架(理论范畴及其转化为研究工具)被认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反映。
自 1960 年代以来,受到多方面批评的逻辑经验主义已分解为多种后实证主义方法,其共同点是对实证主义传统的重新表述。这使它们能够被归类到科学现实主义的标签下,它断言在研究它的人类研究人员的科学审查下,现实的绝对或相对独立性。反过来,这是基于所观察到的现实的客观性与研究它的科学观察者的主观性之间的根本区别。所有类型实在论的共同原则是观察者不属于他所观察到的实在;通过他的科学探究技术,他应该避免任何对现实的介入和影响,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样,观察者的主观性就仅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发现”。
对新实证主义遗产的第一批攻击之一是 Willard Van Ormand Quine (1952),他提出了知识的整体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其限制条件由经验构成的力场。反过来,Mary Hesse (1974) 认为科学语言是一个动态系统,其持续增长是由于自然语言的隐喻扩展。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通过分析科学变革的实际历史发展,挑战科学作为纯粹理性企业的常识性概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科学变革现实的日益增长的认识。考虑到科学实践,他展示了它通常是如何被一种范式统治的,一种被科学界合法化的世界观,在新的范式取代它之前,它仍然占主导地位。
Paul K. Feyerabend 以其“方法论无政府主义”(1975)提出了一种自相矛盾和极端的科学观。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方法仍然是决定和同意哪种理论更适合描述和解释自然和社会世界中的事态的唯一合理程序。当然,理性取决于共同的前提和程序:接受它们的好处是巨大的,因为正是通过它们实现了主体间性。科学客观性既不存在于经典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知识对象中,也不存在于唯心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的主体中,而是存在于当研究人员采用相同的程序并接受这些程序所基于的前提时产生的主体间性。科学研究方法、技术和工具的可重复性确保了结果的可重复性。它们的可重复性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公共程序,易于审查和重新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可能比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更客观,但这是由于自然科学的程序规范化和公开化。没有理由假设自然科学具有特殊的客观态度,而社会科学家具有价值取向的态度。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研究程序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们通常反映了一种通过充满内涵意义的语言表达传达的私人心理状态,通常不是研究界的所有人共享的。
Roy Bashkar (1975)的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一个基于三个领域区别的本体论:真实的、实际的和经验的,主张存在可以独立于我们的知识工作的结构或隐藏机制,但是其力量可以在封闭和开放系统中进行实证研究。这种现实的科学观点也得到了 Rom Harré (1986) 的支持,他强调模型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新现实主义者还提出了社会学的关系范式,以通过结构化理论(Giddens 1984)和社会活动的变革模型(Bhaskar 1989)。根据这种新范式,社会结构应被视为无所不在的条件和人类有意行为的不断再生产的结果。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应用理性主义认同这一观点,他系统地应用关系概念,并有条不紊地将他的理论模型与不同研究方法的结果的经验材料进行比较 (Bourdieu et al. 1973)。新现实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性观点,加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变革性观念,产生了批判性的自然主义它认为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传统都依赖于自然科学的相同实证主义概念。这种批判的自然主义认为,实际上,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都易于科学解释,尽管是不同的种类(Bhaskar 1989)。
这种现实主义观点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受到建构主义运动的严重挑战。,引发了社会学史上第三次且仍在进行中的认识论辩论。建构主义主张将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与观察者的主观现实统一起来。基本原理是所调查的现实和用于调查它的科学具有同样主观的起源,这意味着所观察到的现实“取决于”观察者。这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否认观察者的自主现实的实际存在,而是通过科学知识对这种外部现实的“客观”表示是不可能的。所有关于现实的说法都不可避免地是观察者的“建构”(von Foerster 1984),而观察者又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一个“黑匣子” 其内部成分是不可观察的。因此,即使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现实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客观性,它的自主存在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简单的主观和任意的经验。“构建”的是知识而不是现实(Von Glasersfeld 1987)。
有不同类型的建构主义。最激进的人 (Von Glasersfeld 1995) 坚持认为,除了观察者观察到的琐碎验证之外,即使观察者也不能说什么。不可知的观察者面对的是不可知的现实。一种更为温和的建构主义认为观察者的理论仍然可能存在,即使它否认所观察到的现实具有相同的可能性(Maturana 1988)。最后,有一种建构主义接受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理论,将它们视为心理系统(Luhmann 1990)。
正如当前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立场只是显得相距甚远。特别是当他们从更抽象的理论转向实证研究时,各自的立场变得更加模糊、模糊和重叠。此外,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之间的旧分歧可能会慢慢消失。尽管定量研究技术似乎比定性方法更精确和严格(具有标准化和可重复性特征),但很难证明对所有类型的社会学数据使用量化是合理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并非社会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可以服从量化规则。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认为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和技术是互补的。然而,这种综合和多元的方法需要明确的认识论来证明。因此,尽管已经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一些尝试,但为新兴的综合和多元方法论建立新的认识论基础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第一次尝试是生态范式格雷戈里·贝特森 (1972)。受他在 1940 年代参与由冯诺依曼、香农、冯福斯特和维纳等人组成的控制论跨学科研究小组的强烈影响,他随后围绕几个中心控制论概念组织了他在不同领域的所有后续工作,包括分裂发生、循环沟通和反馈。在这种新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种认识论,旨在超越观察者的内部和外部组成部分之间的界限,即“思想”,被视为一个创始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主体的身份溶化在其生态环境中,在主观意义、行动和行动客观的关系中。尽管贝特森
从历史上看,第二次尝试可以追溯到埃德加·莫林 (Edgar Morin) 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通用方法 (Morin 1977, 1980, 1986),该方法可以根据方法论的多样性应用于各个知识领域。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克服传统科学范式的缺点,他认为这种范式是脱节的、还原的和简化的,因为它没有考虑现实的复杂性。现实的多维性正是他非常全面地尝试建立一种基于自动生态组织的新认识论的出发点。原则。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物学偏见影响的尝试似乎非常不适合社会科学。
最后,Costantino Cipolla 提出了一种基于宽容认识论的新关联范式。(Cipolla 1997)它更喜欢“相互”和“共同”的观点,将传统上相反的认识论极点联系在一起并整合在一起,试图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方法。这种新的关联范式更接近前两次尝试的社会学传统,同时考虑了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原因,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客观现实与主观观察者之间的联系、关系和联系上。以避免任何一极的绝对主义。正是从这种对现实的二元概念出发——它认为现实既是自主的,又是由主体“建构”的,主体又是现实社会力量的产物,归纳程序作为归纳和演绎、特殊和一般、理论假设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双重运动”,超越了任何自足的还原论一元论。
任何对知识基础和方法的系统阐述都构成了认识论。标准的数学认识论在公理自明中找到了这样的基础,在证明方法中找到了方法。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还强调了实验验证的方法。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出现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顽固的认识论分歧的领域。一方面是那些坚持自然科学是获取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的唯一有效模型的人,因此社会科学应该努力效仿它们的方法论先例。另一方面是那些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和创造与自然科学家所关注的事件和对象在种类上不同的人,他们需要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法和理解方法。严格来说,这些替代方案是不兼容的;没有完美的妥协是可能的。
在 19 世纪中叶明显出现的分歧在于不同的哲学先例和学术传统。在一个统一的科学的一边是孔德“小号‘实证’这蒙上社会为最终和最复杂的东西变得可用在人类认知和服从的进化过程中的感觉,如果没有精确的实验操作,然后进行足够严格的受控比较查询,以产生相应的知识。孔德'小号实证哲学的课程(1830 - 1842年)落成了他创造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每一位一样自然它的前辈,但清楚地反映了人的两种理性é笛卡尔和经验主义艾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孔德“最具影响力的认识论继承人É英里涂尔干,谁需要特别的痛苦从,在他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作社会学的区分心理的经验领域。前者同时包含了所有人类的共同点和他们中的一个人的特质。后者包括将人类标记为特定集体成员的东西,是“社会事实”的适当领域首先作为外部强加的义务或强制的经验可用于感官。它产生了社会作为“规范秩序”的经典定义。”它允许两种基本的查询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可以用于受控比较服务。其中之一是对足够大的特定案例进行抽样,以揭示模式变量及其统计协变。另一个试图从可能仅从一个案例中提取出一个系统模型,它代表或表达了它的极限。第一个是统计和定量调查的模式,不仅在社会学中,而且在所有社会科学中。二是模型论探究模式——是否严格代数,在很多现代经济学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定性,如涂尔干“自己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与分歧本身有关的是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在自然科学与他所谓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或“心智”或“人文科学”之间的纲领性区分。“后一类包括构成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但它的主要重点是历史探究学科以及 19 世纪后期将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人文科学没有在狄尔泰“小号类型学产生‘知识’,而是产生“理解。”后者是会意立足于自我反思的必要性的模式,因为精神或心灵的objectifications -人类行为和文物-构成其调查的地形是这样的心理状态的意向,信念,价值观和情感恰恰是objectifications。人类科学家理解任何这样的客观化不是在确定其有效原因,而是在根据它所嵌入的更广泛的历史或文化背景来解释其始终特定的“意义”或“意义”。狄尔泰“他的著作遵循圣经诠释学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的观点,他假设解释的过程主要取决于解释者富有想象力和同理心地进入他人生活的能力。他从伊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在其1781、1788和 1790 年发表的三篇批评中同样彻底地将客观与主观彻底分离,从而将物理世界与经验世界彻底分离。至少在他对康德的挪用中,狄尔泰是与他唯一一位稍晚的当代艺术家Max Weber合而为一。
韦伯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地址“客观性的问题,”在人文科学。他认识到特定的评估承诺确实,甚至应该影响人类科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坚持认为,科学家'的研究,适当地进行,应该而且能够产生不外乎事实。他的决议仍然有它的拥护者,但客观性问题本身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持续到他之外。就其一般形式而言,它是反思性认识的结果,即信仰和评价取向通常取决于或取决于其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例如,托尔斯坦·凡勃伦'观察到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被那些与其统治的实际基础最密切相关的智力追求所吸引。从表面上看,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本身的信念和评价取向应该大致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信念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它确实指出需要说明研究人员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正确地假设它们是持久真实或有效的。如此解释,客观性问题激发了三种普遍的反应。一个是孔德“自己的:认知和道德进化的进步主义渲染,假定现代社会已经摆脱了错误和混乱的根源,这些错误和混乱笼罩了欠发达社会的精神和道德景观。
虽然与实证拐点不再,类似的进化论有以J中央地方ü的RGen哈贝马斯“更近的努力重新建立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第二种回应出现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其中客观性问题随着假设每个阶级分化社会的流行观念都是意识形态扭曲,不为真理服务,而是为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服务。
尽管有许多变化,但它在社会制度或社会心理环境中寻求那些允许某些人脱离其出身阶级并因此在限制他们判断的界限之外思考的因素。在什么因而是一个经典的贡献“知识社会学, ” 卡尔·曼海姆“的工作看到了后期eighteenth-和十九世纪初期的世俗,自由的大学合并等因素欧洲。阿尔都塞“的工作,而不是侧重于政治经济结构和个人情况的conjunctures其中一个调查”实验和批判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先前陷入困境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断绝”。虽然再次有许多变化,但第三种回应可能被称为务实。它利用的哲学资源包括康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从韦伯到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 和社会理论家 Niklas Luhmann,它的支持者认为人文科学中适当的智力劳动在启发式和诊断性构建和干预中结束,无论其偶然性或动机如何,都有助于清晰、交流和翻译。几乎没有回归实证主义,但这种回应强调了一种智力装置的分析服务,该装置在自然科学本身的认识论工具包中不断增加显着性:模型。
认识论认识论。认识论的意思是“知识理论”,有时更具体地说是“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术语,认识论(法国,é PIST é mologie,德国,认识论)进入欧洲语言在十九世纪中叶。作为一个主题,它出现在古希腊,无论是在柏拉图在美诺和泰阿泰德的知识讨论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中 他的“科学”知识逻辑著作中的特征,即围绕基本原理组织的知识,从中可以导出其他知识,或者通过这些知识可以解释各种事实。词根episteme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知识”;在近代早期,相应的拉丁词scientia 的意思是“有组织的知识”,特别是适合作为有序的教义体系呈现的那种。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知识理论在各种知识背景下得到检验和讨论。这些包括对一般知识的方法和结构的讨论,尤其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讨论。最重要的知识对象包括上帝和宗教教义、整个自然世界及其特定部分(如天文学、力学或冶金学),以及人性知识,包括人体(医学和生理学)和灵魂或心智。这些话题在大学课程和由此产生的大量文献中以及在大学以外的个别哲学家的作品中都被讨论过,也许是在王子或其他富有的赞助下,但往往不是。欧洲大学是与教会相关的机构,在 12 至 16 世纪因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著作的恢复而焕发活力。它们提供了关于知识如何获得和组织的理论背景,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早期现代思想家,如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 – 1543),开普勒(1571年- 1630),伽利略状物(1564 - 1642年),培根(1561年- 1626年),任é笛卡尔(1596年- 1650),霍布斯(1588年- 1679号文件),斯宾诺莎(1632年- 1677年),戈特弗里德Wilhelm Leibniz (1646 – 1716)、John Locke (1632 – 1704)、George Berkeley (1685 – 1753) 和David Hume (1711 – 1776) 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环境之外。在主要的早期现代哲学家中,只有Immanuel Kant (1724 – 1804) 享有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
新科学最重要的早期现代认识论事件是 1500 年至 1750 年期间“新科学”的兴起。这一事件有时被描述为“科学革命”,尽管它花了 250 年的时间才得以展开并并没有真正构成统一革命。天文学的早期结果(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和光学(透镜理论)通过望远镜和显微镜引发了智力变革,并预示着人类知识将扩展到大大小小的新领域。视觉理论举例说明了从这项初步工作中产生的主题。依靠光学的进步,笛卡尔发展了视觉的生理和认知基础的大胆新概念,挑战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感官的物理和生理操作的正统观念,并构成了他对亚里士多德心智理论的更普遍挑战的一部分。在他完全发展的系统中,笛卡尔诉诸于纯粹理性的考虑(认识论理性主义),以奠定他关于物质和感觉特性(如光和颜色)的新理论的基础。伯克利挑战笛卡尔的
这门新科学在认识论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牛顿力学,它通过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将天体和地球的领域统一起来。艾萨克牛顿(1642 –1727 年)声称他的新进展是通过远离诸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而产生的(尽管牛顿的工作部分是为了直接回应笛卡尔的物理理论),而是依赖于观察和实验。事实上,平方反比定律是通过将单一的数学定律与关于落体和行星运动的各种经验信息拟合而建立的。此外,牛顿并没有假装了解重力是如何工作的。他只是声称身体根据他的法则趋向于彼此。他的科学成就启发了随后的哲学分析,并被用来支持认识论经验主义。
认知与心理学早期的现代理论通常通过人类思维的力量来解释知识的认知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的方案中,已经区分了各种认知能力,包括感官、想象力、记忆力和智力。后来的作者接受了这些基本权力,并将认识论的辩论集中在它们的操作模式、范围和限制上。智力和感官被视为生产知识的自然心理工具。因此,可以通过人类认知能力的力量和可靠性来研究知识的性质和可能性。诸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认识论者一致认为,人类智力本身就具有能力,无需借助感官经验,就能辨别上帝、物质和人类思想的本质或本质。洛克和休谟等经验主义哲学家否认人类智力具有这种力量,并试图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建立在感官体验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人类的心灵与其他动物的心灵仅在程度上不同,并否认人类的认知能力自然地赋予其产品理性的理由。对他来说,对重要事实的了解归结为通过经验规律产生的认知习惯。康德后来区分了对心灵的经验心理学研究(如休谟)和对知识的逻辑或概念基础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认识论作为一个学科领域与经验心理学区分开来(尽管他没有德语中的“认识论”一词)。
秩序与知识体系早期的现代哲学家在大学教学中获得了一种知识秩序,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学科组织。知识分为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和物理的)和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形而上学研究存在本身的本质(现实的基本本质,例如物质及其属性)。物理学包括整个自然世界,从身体或物质的基本属性到对生物(生物学)的研究再到心理学。十八世纪铰接这样的系统,如Encyclop é模具的狄德罗(1713年- 1784年),1717年让乐朗多达朗贝尔(-1783),并在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的高度结构化的哲学体系- 1754年)。这些后来的系统在划分与认知能力相关的知识方面通常与培根一致:历史——这意味着所有事实的集合,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人类社会——以记忆为基础,诗歌(以及更普遍的艺术)以想象为基础,和哲学——既有理论性的,包括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也有实践性的——是基于理性(或智力)。这种分类有时会出现分歧。因此,心理学首先被归类为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后来归为形而上学,然后归为“道德科学”(或“人文科学”),后来又归为自然科学。学科的分类和重新分类仍在继续。
怀疑和限制在早期现代认识论的许多描述中,16 世纪古代怀疑主义的复兴具有显着意义。持怀疑态度的著作确实激发了讨论。在宗教背景下,对人类理解神的能力的怀疑既被用来支持有组织的宗教必须使用其神圣授权的权威来教导关于神的真理和宗教主题的主张,也被用来质疑是否有人可以声称拥有真理关于此类事项。一些哲学家,如旧金山小号á nchez(C 1550 -1623),怀疑人类的理论知识是否真的能像形而上学那样揭示现实的本质,并提出了一个更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知识目标。笛卡尔将怀疑主义用作在形而上学知识中实现确定性的工具,但他本人并没有认真对待怀疑论的威胁。其他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洛克,很快就驳回了怀疑论点。像休谟这样的哲学经验主义者发展了一种缓和的怀疑主义,允许牛顿式的关于自然界经验规律的知识,但否认人类有能力超越这种规律,去认识上帝的存在或所谓的人类灵魂或思想的非物质性。一般来说,早期现代认识论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最终形成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认识论源自希腊语ἐ π ι σ τ ή μ η和λ ό γ ο ς的术语,意思是知识的科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只是指对知识及其问题的调查。同义词是标准学,来自希腊语κ ρ ί ν ω意思是区分或判断,这意味着测试知识以区分真假。见标准(criteriology)。与这些相关的是知识和知识学的表达批判;前者起源于康德,在当代哲学中被大量使用,而后者在欧洲的使用中占主导地位。在经院学者中,所有这些术语都被认为是指关于真实和某些知识的科学。
可以说,认识论在目前的发展状态下,是哲学研究的最新、最未完成、最不令人满意的领域。这也是最有争议的。它的名称、主题,甚至它试图解决的确切问题都没有一致意见。一些重要的哲学家认为它是一门完全综合的学科,它的存在既不是因为现实的要求,也不是因为人类思想的迫切需要,而只是因为需要对错误和误导性的知识理论做出反应。他们的观点似乎是,整体现实主义不必,甚至不可能是批判性的。然而,事实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存在。这确保了认识论在哲学学科中的适当位置。
希腊和中世纪起源。由于人们总是问关于知识的问题,并且总是关心区分真假,因此认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之前,人们对知识的兴趣比对自然世界的兴趣低是很自然的。然而,深入自然秘密的困难导致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事实上,宇宙学系统的多样性引起了诡辩者的怀疑。因为犯了很多错误,怀疑论者很容易听到他声称真理是无法实现的说法。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深刻思想才对这种早期的怀疑主义产生了反应,在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中可以找到真正科学认识论的起源。特别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现在可以被认为是主要认识论传统的有序陈述开始了,这种陈述符合普通人的常识,但远远超出了后者的原始指示。这一传统的主要思想是承认感官知识和智力知识之间的差异;以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感官内容为基础的智力的抽象知识;否认先天性;抽象理论的概要;以及一般而言,被称为温和实在论的学说复合体,其中平衡的共相学说使哲学和科学成为可能。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唯物主义迅速衰落,随之而来的怀疑主义。这种态度大致持续到圣奥古斯丁时代,在圣奥古斯丁时代,他强调启蒙理论,并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激进理智主义。奥古斯丁的观点在中世纪早期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在高学术时期被抵消,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恢复,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纳入西方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的联合现实主义的综合中达到了顶峰,尽管它也引起了与布拉班特的 siger 的拉丁语 averroism 相关的认识论困难(参见双重真理,理论)。
在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之后,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让位于唯名主义,这反过来又为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回归铺平了道路。有人企图重振红衣主教托马索·德比奥CA火星相棋,西尔维斯特ferrariensis,旧金山苏的作品上了年纪的认识论传统Á苏亚雷斯,和ST的约翰。托马斯。然而,结果是零星的,这些人的影响力受到严重限制。
现代发展。的反知识分子趋势的扭转真的只用仁开始é笛卡尔,谁发起的一项活动,恢复理智的权利,并在这样做成为现代哲学之父。尽管笛卡尔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但他却是一位糟糕的认识论者,这仅仅是因为他试图将数学方法论应用于所有知识领域。此外,他不健全的心理使他的认识论学说因自那时以来一直困扰着知识科学的假设而败坏。笛卡尔否认感觉的真正价值;他重新引入了柏拉图与生俱来的思想,并对表征主义的知识概念负责——一个一直被归咎于经院学者的观念,尽管他们从未坚持过。笛卡尔的意图是最好的;他本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并捍卫理性的首要地位,但他的预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并且他只是成功地培养了一种仍然混淆当代思想的精神和物质的绝对二元论。
认识论在笛卡尔之后退化,直到 18 世纪末,康德开始了一场哲学革命,提议消除所有无根据的假设并对知识进行真正的批判。康德在这里没有成功,尽管他将敏锐而有条不紊的智慧、坚持不懈的劳动和卓越的意图用于哲学服务。因为他非常聪明,而且对他之前的长期认识论传统一无所知。忽略了人类的智力知识是抽象的这一事实——这一事实迫使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承认人类智力中的抽象力量——康德认为,在他拒绝接受的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先天思想和他自己的理论之间别无选择,后者将智能告知感性数据并将其自己的形式强加于这些数据。对他来说,头脑使事物变得可理解,并将可理解性强加于它们;真实本身是不可知的。在这种观点下,形而上学变得不可能,知识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告终。康德预见到他的思辨理论将导致的僵局,于是发展了他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并为自愿主义和实用主义铺平了道路。认识论中的当代唯心主义也源于康德。与之相反的是可追溯到 D 的思路。
认识论问题。过去 50 年编写的关于认识论的教科书和论文经常相互矛盾,提供完全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基本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与笛卡尔、康德和休谟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作斗争的全神贯注在促进普遍混乱方面发挥了作用。防御性和否定主义标志着大多数在经院传统中发展认识论的尝试。然而认识论并不是消极的。这是对知识的积极调查。鉴于理性的本性和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它必须断言对知识的真正要求,而不是防御性的主张。
尽管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都没有写出完全是认识论的论文,但他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利用了对知识的积极和科学有序的批判。由于这与他们关于许多主题的著作中的不同内容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来揭示其精确的认识论意义。在下文中试图勾勒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主义文集隐含的基本认识论问题,就已经被LM [R提供了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过分依赖é GIS(见bibliog)。
圣托马斯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指出,在对任何事物进行适当的科学调查时,只能提出四种类型的问题。它们是:事物存在吗?它是什么?它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它有这些特性?(在 2 肛门。帖子。1.2)。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与本质和存在的构成有关,而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与实体和偶然的构成有关。通常,第一个问题不会出现,因为对于感官或智力来说,事物的存在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余三个问题的答案,以一系列演示形式表述,构成了该特定主题的科学。很明显,在许多情况下,所寻求的知识将是广泛的,并会引起大量的进一步问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人类智力的不完善或所调查事项的困难都可能导致难以或不可能进行任何长时间的调查。
应用于认识论,这种基本方法论提出了关于知识的四个问题:有知识吗?什么是知识?知识的属性是什么?为什么它有这些特性?但是知识是直接经验的事实,因此不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因此,整个认识论研究可以归入其余三个问题。
知识的本质。至于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知识在人的经验中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活动,这些活动发生在内部,但又使人与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接触。对知识的研究本身就属于心理学,而认识论正是从这门科学中接受其基本原则的。理解知识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道不是一种物理、化学或机械活动,而是一种仅存在于生物中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动。与瞬态活动不可还原地不同,它是自我完善的,并在它起源的代理中终止。这意味着知识是人的一种品质,一种自我修改,其形式类型由其与主体以外的事物(即已知对象或事物)的关系指定。
主客体悖论突出了知识的一个神秘方面,它使所有认识论问题复杂化。认识的全部内在性强调主观因素,必须给予适当的关注——尽管这里过多的关注会导致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知识要求人们认识到它的外在性,因为知识使认识者以外的事物呈现给他。因此,认识论研究的第一个领域是对这种主客体关系的解释。其内在性及其同时的外在性的阐明必须与认知操作的内在性和自我完善性有关(见意向性;客观性;意识)。
知识的属性。认识论研究的第二个一般领域与问题的答案有关,知识的属性是什么?更准确地说,它与真假的属性有关。一种真理与感官和智力层面上的忧虑知识有关(见忧虑,简单)。这个真理来自于认识能力与其各自对象之间的必然关系;它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内置到认知操作中,因为这些在理解中可能不是错误的。这种真理虽然自然得到保证,但并不完美;的确,它与作为其财产的令人担忧的知识一样不完善。忧虑的知识,事物的简单介绍,在感官和智力层面上提供现实的点点滴滴。它使人们能够掌握事物的孤立方面,而无需统一这些方面,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在现实中发现的。
真正的真理问题是在智力水平上统一这种令人担忧的知识的问题。人类的智慧对统一有着强烈的渴望,这导致它整合通过忧虑获得的零碎知识。这种统一是由一个判断或一系列判断带来的。当这种统一的方式足以满足现实中的实际统一时,心灵判断就会产生一个正确的命题或陈述。相反,当命题与现实中被发现的方式不一致时,结果是错误的。因此,真理的可能性就隐含在理解和判断这两种智力功能之间的差异中。而前者只是向头脑呈现一个对象,后者是一种动态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头脑不仅报告它所看到的事物,而且表明立场并对它们说些什么。正是在这种表述中,才能正确地发现真假。围绕真理、判断、阐释以及至少某些判断可能适用于现实的保证的问题构成了认识论探究的第二个领域。
属性说明。认识论者面临的第三个普遍问题是:为什么知识必须有真或假?人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提出问题,例如,什么是绝对可靠的知识?后一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极其复杂的大量问题。第一个问题必然涉及人类智力必须无误地知道的真理的存在,它不能错过,这些真理是由它必须拥有且无法避免拥有的知识强加给它的。如果有这样的真理,重要的是要发现它们是什么,然后拥有它们,探究如何将它们用于进一步调查现实。
圣托马斯非常确定第一原理存在并且可以,事实上,必须是已知的。“在它的起源中,所有的知识都在于意识到第一个无法证明的原则”(De ver. 10.6)。“在被理解的事物中可以找到一定的顺序。我们在任何其他事物之前掌握并包含在每一个理解中的概念是存在。存在和非存在的概念基于第一个无法证明的原则,即,同一件事不能同时被肯定和否定。反过来,所有其他原则都以这个原则为基础”(Summa Theologiae1a2ae,94.2)。这里开始了所有的确定性,一种首先来自必要判断的真理属性。但是圣托马斯非常清楚地警告说,这不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句话。正确理解这些原则的知识是无误的,但这些是“人类探索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来自自然而不是因为我们寻求真理”(C. gent. 3.37)。
第一性原理的知识是模糊和笼统的;它提供了关于所有事物最普遍特征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但没有提及更详细和特定的品质。这些必须被找出来,而不能从一般真理中推导出来,尽管后者总是控制着更特殊的真理。基本原理的知识并不能提供最终的答案,而只是起点,人类的理性在充分了解它所拥有的控制并确保正确应用这些原理的绝对有效性的情况下,可以继续进行长期寻找更详细的真相往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思想的首要原则是所有智力建构的基础。此外,还有
从由感官提供的更多材料中,智力感知到首先属于特定知识秩序的其他原则。圣托马斯在De veritate的开头分析了这些判断的精确形式(1.1)。这样的判断只是人类心灵在检查现实时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主要精神认同,无论是在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一般模式方面还是在人类经验中适用于不同种类事物的特殊模式方面。与一般存在方式有关的判断涉及先验,是形而上学所有原则和结论的来源。与特殊存在方式相关的判断涉及现实的范畴或各种类型,是特殊科学的所有原理和结论的来源(见科学,分类)。因此,对任何判断的真实性的最终检验是该判断的解析解析回到首要原则,这就是圣托马斯可以说的原因:“德弗。1.12)。人类的智力不会学习这些原则,也不会假设它们;一旦它获得了构成它们的术语的知识,它就会自然地、必然地、立即地到达它们。
因此,人类的头脑通过掌握首要原则,然后从这些原则出发得出结论,从而获得真理和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可以从这些原则中推导出来,而只是在推导出任何东西之前,必须承认并应用它们。至于偶然的事物,例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根据基本原理——包括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和所涉及的特殊科学的第一原理——来研究、衡量和测量物质。将这些原理应用到经验数据中,就可以得出特定科学的结论。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真理,然后他才能从中继续了解其他真理。换句话说,人不仅可以达到真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达到真理;有些真理他不能错过。正如圣托马斯在这方面所说的那样:“虽然没有人能够达到对真理的完美理解,但没有人会被完全剥夺,以至于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的知识很容易,立即我们得出真理的明显原则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在 2 meta.1.275)。与推理过程相关的认识论问题包括,例如,对推理过程本身的检查;对各种推理类型的检查,例如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最后是结论借用原则的证据的有效性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只有部分或不充分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根本没有解决方案。认识论者的工作是在合理的逻辑、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