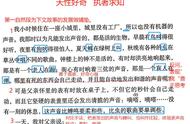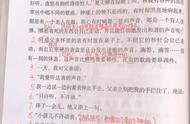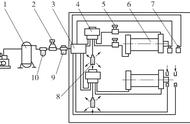里尔克诗选
秀陶/译①
时辰之书(Das Stunden-Buch)
I 2
我寓居于这日益扩张的,
围绕下界运行的弧内。
也许我将不克持久,
但我将勉力以图。
我围绕着神以及古塔打转,
以我古老的方式绕行了千百年。
但我仍不知我是一只隼鹰,
一个风暴,还是一支伟大的歌。
I 6
你,我紧邻的神呵,要是晚上什么时候
我猛烈的敲击把你吵醒,皆因
我几乎听不见你的声息,
而我知道:你就是一个人在隔壁。
要是你想喝口水,没有人
端来给你。你只是在暗中摸索。
我一直在听。只要一声轻轻的招呼
我就会马上过来。
我们之间只有一堵薄墙
偶尔只要
来自你或我的一声轻唤
它就会无声地
倒塌。
那墙就是以你的形象砌成的。
它挡在你面前,像你的名字一样遮掩你,
而当我内中的光辉高焕时,
我的深心因而认知你
那闪耀即成白费,一似虚掷于相框的光。
然后我所有的意识就变得跛残,
自你处流放以至无家可归。
I 36
神呵,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我是你的水罐(要是我破碎了呢?)
我是你的饮料(要是我腐败了呢?)
我是你的衣衫,你的行业
失去我,你也失去了意义。
没有了我,你将无家可归
无温暖亲切的奉迎。
我是你的绒鞋
将自你疲乏的双脚脱落。
你的大衣也将跌下。
你的顾瞥,那投于我温暖的
颊上的,仿佛歇在软枕上的,行将
枉然无尽地寻索——
且一似夕阳一样躺落
于异乡山岩的膝下。
你怎么办呢,神呵,我焦急不安哩。
II 7
熄灭我的双眼,我仍能看见你。
堵闭我的两耳,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仍能走向你。
没有嘴我仍能祈求你。
卸去双臂,
我以心代臂拥抱你。
停止我的心,我用脑跳动。
要是你在我脑内纵火
我的血液必仍然承载你。
杜伊诺哀歌
第一哀歌(Die erste Elegie)
当我哭喊,谁会在天使群中
应我?即使他们中的一个会突然
拥我入怀,我也会因他强不可抗拒的
存在而消竭。因为美不是别的
而是恐惧的开端,我们几乎难以承受
我们之所以如许的景从他们皆因他们
轻而易举地便能摧毁我们。每个天使都可怕。
——所以我极力抑制,忍嗌
而吞声。呵那么当我们需要时
有谁可投靠呢?不是天使,不是人,
连明察的畜生们都意觉到
在这暧昧的世上我们
一点也不自在。也许在山坡上
还留下一棵树,我们可以日复一日地
望一眼。一条昨日的街道,
以及忠实的恋栈我们
而不欲离去的习惯。
——呵,还有夜,我们所期望的,当风满含空宇
啮咬我们的脸——她将为任何人滞留。
温柔而略带失望的莅临与孤寂的心
会合。对于恋人们她是否就会宽待一点呢?
呵,他们只是彼此遮掩他们的命运。
你仍不明白么?掷你满怀的空无
于我们呼吸的空间吧,可能鸟雀们
会感到空气被稀释而更需振翅狂飞。
是的,春天需要你,众多的星子
待你顾瞥。往昔的浪涛
向你汹涌,或当你行过
一面开启的窗,一只提琴
做出自供。这些便是你的使命
你能完成么?你不是常被
希望分心么?仿佛一切都
应诺过你一个爱侣?(你将在何处藏娇,
这些奇思怪想
入出翻腾,常竟夜不去。)
如果你期待,歌颂伟大的恋人们;
而他们虽激情卓著,却远非不朽,
一些被遗弃者,你几乎嫉妒,
他们比你曾爱过的人,或会更爱你。
从头来过吧,再试试你无力的赞颂;
记住英雄是不死的,即使暂灭
也是为了另世的重生。
力竭的造物者将爱人们召回
到她那里,又仿佛不够精力将他们
再造。还能记得
迦丝芭拉·丝坦帕②么?为了那伟大的爱情
每个被爱人遗弃的女子
或会自叹“要是我能像她就好了”。
这亘古的苦痛现在不应为我们
结点果么?还不到时候让我们
自被爱者释放么?我们战栗、隐忍
就如箭忍受弓弦,以便在那积聚的一跃
来增益自己。毕竟无地以停驻。
声音,声音,我的心啊,听吧,一似
圣哲般谛听。亦非你就消受得
神的语音。只是听得那长叹
那自寂静滋生的无止的信息,
自夭折者瑟瑟地向你而来。
在你进入罗马或那不勒斯一教堂
他们不曾向你倾诉他们的命数?
或者高处的铭刻向你显示
就像去年在至美圣玛丽亚堂那块石刻
他们向我要求什么?或是要我抛弃那
因他们死亡而不平的面容,因那会使得
他们的精灵颇为受阻。
当然,不再如往昔样
总有无尽渴切的手提携;
就连旧日的名字也如破玩具样抛掉。
不惯的是昔日的希求也都放弃了,
不惯的是昔日的老关系也在空中
飘散。在开始觉出一丝永恒
之前,犹想极力挽救,
困难的死呵。但活人的错是
将生死之异认得太绝对。
天使们(有人说)常分不清
他们是在阳间还是阴间。
永恒的洪水,涌向阴阳间所有的
世代,并将他们的声音淹没。
毕竟那些早夭的不再需要我们,
他们与尘世分离,就像婴儿轻巧
地断奶,与母亲的乳房隔绝一样。但是我们
就是要这样巨大的神奇。烦恼就是赐给我们的
前进的源泉——没有这些我们活得了么?
传说是无意识的么,有次在哀悼里诺③时,
第一个无畏的乐音穿透了洪荒的麻痹
在惊呆了的空间蓦然地一个如神的
青年离去。那空间第一次感受的
和鸣,至今仍愉悦,支撑并慰安我们?
注解:
① 译者秀陶 (1934-2020),生于湖北鄂城。1950年到了台湾, 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来加入纪弦创立的“现代派”诗社。1962年远赴西贡。1970年代移民美国,先于纽约,后居洛杉矶。以上译作采自他的译著《最好的里尔克》,所选作品涵盖了里尔克的主要作品和名篇,最大限度避免了里氏爱好者的遗珠之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刊行。
② Gaspara Stampa (1523—1554),意大利女诗人。因遭爱人特雷维斯(Trevisa)太子抛弃,乃有大量十四行诗创作。
③ Linos,希腊神话中与奥非乌斯同时之诗人。由于他的死乃有哀乐之产生。

海岱山下读冯至
张清华/著
我想象不出,七十年的时光会埋葬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七十年的历史风尘,需要经过怎样的擦拭才能透见初时的踪影。七十年前,那个二十五岁的中国青年,怀着他的幻想和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冯至。而今,这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然进入历史,化作了书中的人物。
冯至一直不认同“海德堡”(Heidelberg)这个译名,因为这里这个“堡”字实际只是“山”的意思,而其音译也应该叫作“贝格”,准确的译法应叫作“海德贝格”,比较传神的和“雅”些的译法,则最好叫“海岱山”,因为“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但因为习惯,他个人也“只手难挽狂澜”。在好几篇文章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想,这大概和他那时在这里生活的诗意的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海岱山”,的确是个更富诗意和美感的名字。不过听起来却不像是个西域之地,倒有点像是个东方海上的仙山蜃景的意思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叫“海德堡”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海德堡也的确是有一个历史很悠久、规模也相当雄伟的古“堡”呢。
1930年10月,冯至来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曾转学柏林大学。1935年6月,他在海德堡以一篇论诺瓦利斯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海德堡是冯至德国之旅的最重要一站。这里的山山水水该留下了他密密的足迹,这里美丽的景色和渊长的文学传统,曾给了他丰厚的滋养和创作的灵感。
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藏书馆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搜寻冯至的书,结果不算理想,只找到了一本集有散文和文学随笔的《冯至选集》的第二卷,和一本配有德文翻译的汉德对照本的《十四行集》,本打算再系统地翻读一下他的诗作,但也只有这一点了。倒是另外翻到两本厚厚的《冯至学术论集》,只是我的兴趣恰恰在于他的诗歌。虽说翻阅其他的合集和各种选本也还可以见到一些,但已是一鳞半爪,无法集中读出全貌。想来惭愧,我是号称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人,然而对冯至的诗歌却素无多少深入的研读。说真的,过去我读他的诗,除了对他的《吹箫人》等几首长诗有格外好的印象,对他的抒情诗总的感觉是比较僵硬刻板,且有看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韩波砍柴》那类半生不熟的“假民歌”时倒胃口的记忆,便由浅见再加上偏见,一直不愿细读。此刻在遥远的异国,踏着七十年前诗人走过的河边小径,我展读他的十四行时,忽然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从中读到了诗人从欧洲文化和德国哲学中带回的种种启示,读到了结束青年时代的热情与忧郁之后,诗人对人生与存在的深邃的体悟:“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生命在临近死亡的片刻闪耀中,显现出存在的全部尖锐性,以及它令人激动和彻悟的欢欣与苦难。诗人深刻地体察出了生命的脆弱,但又深信着那彗星般的历程中意义的不言自明,深信那渺小的个体里充盈的美好记忆与凛然的尊严。这些句子让我充满了感动,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这是开卷的第一首。用渺小的存在持守生命的启示与尊严,这质朴的诗意显得格外博大和坚强。在此前的新诗中,可以说没有谁会这样写,不管是那些自我扩张的、悠闲绅士的,还是忧郁悲情的、晦暗绝望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这样的事物,并如此感动着“提前到来的死亡”。它让我相信,再弱小的生命在它们的存在里,也闪现出创造的意志与智慧的光芒,它们燃烧着消失,由于死亡而存在,就像一颗颗天地之间巡弋的流星。这是多么壮丽的理念,令我豁然而心惊。我一下子改变了对诗人的看法。
事实上,冯至早期的诗虽然也声称受了里尔克的影响,但总的来说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句法和语感不那么流畅,思想也绝对没有如此深邃。在他写于1979年的一篇《自传》(大约至少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中,冯至称自己在海德堡“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凡·高和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的诗歌写作却是一个空白。虽然有些译作,但自己却“写不出来”,这的确令人奇怪。他在这篇《自传》中,将之归咎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复杂斗争中”,自己“却无视现实……”云云。请注意,他这时说自己在接受上述影响的时候,心态不免有些“微妙”,他当然掩饰不住有一点得意与优越感,但又用了一个“却”字。这言不由衷的表白和“自我批评”显然有些酸意,只是考虑到刚刚度过了极左年代的心中余悸,这样的说法也还是可以原谅。最真实的情况,我想应该是由于他年轻时代的情感方式受到了强烈震撼的缘故。人常常是这样,当他对一件事物或一种思想还未完全弄通时,总是大着胆子评头论足,等到他真的弄懂了,大约又因为敬畏而沉默,我想冯至就是这样。年轻时代喜欢的是表皮,“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还有那“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等等,但1936年,他真正读懂了里尔克,也读懂了荷尔德林,明白了他们的写作只取材于“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而作》),几年后,他恰恰是在战争的间隙里,在避乱的山居小屋里昏暗的油灯底下,开始了同样境界的写作。读1941年他的二十七首十四行,我的灵魂感到颤抖。
一个诗人不可能没有弱点,作为完整地经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冯至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例证。他十六岁开始写诗,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即参加上海“浅草社”的文学活动,1925年二十岁时又参与发起“沉钟社”,之后在很多年里还一直得到鲁迅这样的前辈的鼓励,他的写作一开始就通过他研究德国文学的叔父冯文潜而受到德语诗歌注重智性与思想内涵的传统的影响,并由此延伸为受德国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这才有了他自己所说的“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即20年代的《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时期,以及40年代的《十四行集》时期。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写出了《十四行集》的冯至,后来又写了《韩波砍柴》那样的作品。一个那么有天赋和造诣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倒人胃口的鹦鹉学舌者。现在想来,我们当然会说,一个诗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与个性去写作,按照艺术原则去写作的话,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冯至如果活着,自然无法回答这样的追问。但事实却是他根本无法沉默,所有的诗人都参与并共同制造了那个假民歌的时代,郭沫若、艾青也一样,闻一多如果活着恐也不能免俗,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的悲剧。
在冯至的那些学术研究著作中,也可以读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学术思想贫乏的时代病。无论是他对杜甫的研究,还是对歌德、海涅和德国文学的研究,除了翻来覆去的思想性的阐发对照、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辨别,确实难以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也颇令人悲哀,一个有过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学者,其学术论著的思想与精神含量何以会如此贫瘠?我特别想能够读一读他当年研究诺瓦利斯的那篇博士论文,看看它是什么模样,想必那与他后来的学术论著是大相径庭的。但翻遍那些著作,却寻不见踪影。
1979、1982和1987年,冯至曾三度重访故地海德堡。那已是整整四十五年之后了,翩翩少年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我没有读到他专门回忆海德堡的文章,但读到了一篇写于1981年的《涅卡河畔》,那是写他坐在上游的图宾根追念下游的海德堡读书经历,以及追怀诗人荷尔德林的一篇文章,他写到自己“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四十五年前”,“那时我常在夕阳西下时,坐在流过海岱山的涅卡河畔的长椅上”的情景,很让我感动。不知那一刻他是否还想过自己漫长的一生,虽然他写下的是一个又被革命和政治曲解了的荷尔德林,但我想他那一刻肯定也有几分凄然与恨悔,风雨苍茫,世事变迁,一个人奔忙一世,耕耘一生,留下了多少?如果他还是一个诗人,他应该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检视,他知道将会留下什么,而另一些东西将被湮没进时光的废墟。想到这里,他应该眼含一颗老泪,长叹一声。
我眼前出现了那个老人的幻影,河边的长椅上,我听见他正发出那样一声叹息。
注解:
作者张清华,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海德堡笔记》为作者在海德堡大学讲学间隙的欧游杂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