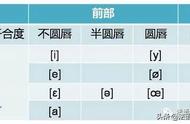故事由人物构成。纵观哲学史,我们发现几种基本类型的思想家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人们还是把他们都看作“哲学家”。
我把第一类思想家称为“求知者”(the Curiosus),这是哲学史上极易被遗忘的类型。本书中的一个要点就是揭秘他们在历史上被埋没的原因。求知者代表了这样一群哲学家:他们详述暴雨和飓风的成因,磁变的原理还有跳蚤翅膀上细小颗粒的分布。值得一提的是,精通近代早期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求知者以女性为主。
求知者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认为,研究具体(res singulars)事物的知识没什么丢人的。这些知识同样可以组成一个整体,将自然的秩序揭示出来。他们也把发现这一秩序视作哲学家的要务。有人匿名批评亚里士多德醉心于研究海洋生物学,亚里士多德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说辞为自己辩护,来解释为什么要研究海参或头足纲生物的内脏。这一辩护词也成了这种哲学研究方法的标准概括:赫拉克利特懒洋洋地裸身躺在炉子上,一位尊贵的客人撞见他这样时,他应答道:“这里也住着神。”亚里士多德援引这一格言,希望借此立场明确地捍卫动物学研究的哲学价值。求知者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常见形象,比科学家出现得还要早一些;同时,他们也是最后一批认为上帝存在于具体自然事物之中的哲学家。
圣人(the Sage)是哲学家的第二种身份。这可能是哲学家最古老的社会角色,比“哲学家”(philosophos)这个词还要早几千年。在这里,我们应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这一身份,包括那些社会上广受尊敬的人——他们往往富有口才,被看作能沟通内在与超验领域的中间人。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能传达众神的旨意,或能够解释超出人类经验之外的事情。比如,这群人里包括注解印度教神圣经文的婆罗门,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印度古典哲学的文本基础。直到某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才用清晰的概念和有效的论证来描述祭司的“中间人”身份;也只有当祭司的形象出现在类似的文本中时,我们才开始觉得祭司的行为是哲学或准哲学的。萨满或在非文本文化中的类似形象完全符合“圣人”这一角色。这一角色通常由女性或是较阴柔的男性担任,虽然扮演这一角色的女性常常得不到社会和体制广泛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法语中“助产士”(sage-femme)一词的文本含义就是“有智慧的女人”或是“女圣人”。在大众眼中,她们拥有关于人体和人在自然界之中的地位有关的智慧。
哲学家的第三种身份是“牛虻”(the Gadfly)。“牛虻”们认为,哲学家既不扮演着神圣与世俗之间沟通者的社会角色,也不是避世的隐士,而是要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纠正他们自己社会成员的见识短浅和误解。苏格拉底算是“牛虻”中的特例,因为他没有制订一个积极的计划,来取代他同时代人们的许多错误信念与意图。相比之下,许多社会评论家或尽忠职守的哲学家们都遵循了这一可敬,而且仍旧非常重要的传统。
禁欲者(the Ascetic)是哲学家的第四种身份,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他们出现的时期称作“轴心时代”。12此时,佛教和基督教登上世界舞台,二者均明确反对生活在华丽庙宇中的祭司们的权威。犬儒主义者、耆那教徒(他们被古希腊人称作裸体主义者或是赤身智者)、早期基督教徒,还有其他的弃世者们为哲学概念提供了一种观念的范本。按这种观念来看,哲学的第一要义应当教人顺应自然或是神圣法则,要不就是服从于某种高于社会、国家或神殿虚假权威的事物。苦修者一直是中世纪哲学中一个为人熟知的形象。虽然现在这一群体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修道院中,但这一形象之后的效仿者也有世俗的现代人,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通常被视作一个个例,但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到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禁欲者”已经不再是一种特征显著的社会角色,所以尼采没法按传统的方式做一名“禁欲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哲学风格的禁欲主义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
士大夫(the Mandarin)是哲学家的第五种身份。虽然与朝臣(Courtier,即将介绍的另一种身份)不同,但它仍是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术语。“士大夫”描述的是一个阶级,而不是某个脱离了这一阶级的特立独行者。这个词源于中国帝国时代(Imperial China)选拔精英阶层的科举制度,而且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现在法国选拔“高师人”(normaliens)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可以与英美国家的精英教育体系稍微扯上些关系,因为当今大多数在哲学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人都来自这一体系。不论在哪里,只要士大夫身在朝堂,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全力维护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称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就像一群小心守卫着学科界限的卫兵。许多富裕的资助人赞助他们做哲学:以前是皇室,现在是企业(这一点和“朝臣”的情况一样)。士大夫们离权力的中心也很近(现在的顶尖哲学院校通常地处资本密集的世界大都会附近,可以驾车或者乘火车方便地到达)。但不同于朝臣的是,他们大体上都能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一举动似乎跟金钱没什么关系。此外,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谴责朝臣不得体的行为。然而在即将到来(或许已经到来了)的后大学时代,士大夫们的前途实在是未卜。
最后一个角色是朝臣(the Courtier),也是哲学家的第六种身份。这一形象不仅广为人知,而且备遭轻视。在一本最近流行的书里,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被塑造成高贵的苦修者13,以此对比莱布尼茨(Leibniz)的“不择手段”——因为后者准备将哲学服务卖给出价最高的欧洲国家。作者之所以对两者的社会角色做了如此截然的区分,只是希望读者能够明白,斯宾诺莎本质上是更好的哲学家。这就好比我们认为一个人不能兼具野心和智慧,同样,一个在世俗中摸爬滚打的人不可能同时是一名深刻的思想家。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朝臣”。当这一身份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时,与它挂钩的显著特征就是金钱(尽管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某些在寺庙里当祭司的圣人)。最近,朝臣常以“叛徒”的面貌出现,不过我们也可以委婉地将他们称作“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牛虻”,他们的志向并不在于改变社会,而是为了升官或者出名(此处的性别代词是有意的,因为这一形象大多是男性)。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这一描述呢?所有的哲学家都需要支持,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足够坚强有力的意志,选择坚持纯粹的禁欲主义。对于朝臣这一角色而言,他们把追求尘世的财富和荣耀视作自己的终极目标,而不是作为他们对智慧的纯粹热爱的附属品。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这些人在隐瞒他们所追求的是财富和荣誉这个事实上做得非常糟糕。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所渴求的东西是否完全与深刻的思想无法相容?莱布尼茨似乎为“不相容”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反例。但还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亟待解决,它的答案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与哲学本质有关的内容:当人们质疑某位哲学家的品德时,为什么一直都把“朝臣”的身份作为人身攻击的有力武器来使用呢?
与康德的十二知性范畴不同,我对哲学家的六种分类既不详尽,也并非通过严格的演绎推导得来;在没有进行大量的修订和补充之前,它都算不上一种成熟严谨的分类法。比如说,有人可能也想把冒充内行的人(Charlatan)算上:这些自学成才的大师们往往会夸下海口,自诩有求必应,无所不能。但是我们会发现,要想完全理解那些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被称作哲学家的人们的毕生事业,还有他们造成的社会影响,只需哲学家的这六组群像(还有介于这六种类型之间的形象)就够了。
(本文节选自《哲学家的六张面孔》)

《哲学家的六张面孔》
[美]贾斯汀·史密斯 著
新华出版社 2017年11月
ISBN:978-7-5166-3481-3
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