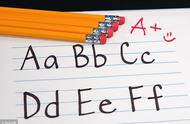小学之名,最初是指初级学校,《礼记·王制》篇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说文解字·叙》引《周礼》称“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白虎通》说:“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这些典籍提到的小学,都是与大学相对而言的初级学校,这是小学的第一种含义。在中国古代,至少在汉代,小学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指一种专门的学问,以研究中国文字为主,后来随着这种学术的发展,则成为中国古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统称。所以章太炎说:“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1]黄侃说得更为明白:“小学者,中国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2]
作为文献学的方法,小学的含义就是如此,这与古代所说的初级学校的小学不同。小学之所以用来指称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其源有自。因为古代儿童入小学,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认字,其基本方法就是学习“六书”,如前面所说的“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清楚:“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儿童在小学学习六书,主要目的是认字,而不是用六书的方法研究文字,还不是专门的学问,要达到这一步,则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于是小学就有了另一种意义。《汉书·杜邺传》载,“杜邺从张吉学,吉子疏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颜师古注:“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这说明专家学者所研究的小学(文字之学)与儿童所学的认字不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实有渊源关系。
以六书研究文字的小学,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书·平帝纪》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所谓“通知”意即通晓,通晓小学的人,即杜邺这种学者。此类通晓小学的学者在当时已有专门的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所有学术著作分类时,其中就有了“小学”一家,据记载当时有小学十家,著作有四十五篇,包含扬雄和杜林二家二篇在内,可知扬雄和杜林与杜邺一样,也是通晓小学的学者。总之,早在汉代,小学就已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指初级学校的小学,一是指研究文字的专门学问,这两种含义在后来也一直同时使用,所以历代都有称为小学的学校,也有指称以文字学为内容的专门之学——小学。
(二)小学的内容不过后来学者们所讲的小学,主要是指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专门之学,而不是指儿童学习六书的初级学校。自汉代在学术之中分出小学一门以后,以后历代学术门类中都一直保持有这一门类,如《隋书·经籍志》载,曹魏时秘书监荀勖著《新簿》,把各种书籍分为四部,其中的甲部包括六艺(即六经)和小学等书,南朝齐的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其中“经典志”包括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类书籍。之后四部的名目与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小学一类也一直包括在经部之内,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其内容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即黄侃所说的小学。
把文字、音韵、训诂统一为一门学问,而称之为小学,这种观念奠定于清代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最喜欢对古代经典中的文本及典章制度进行考据,这都须从具体的文字及其音韵和训诂入手,故他们特别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并将此三门合为一体,认为绝对不可以分割成互不相*学问,必须在研究古代经典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便考据古代经典中的各种问题,认为这是一切学问的根基,故统称之为小学。对于古代经典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如果都搞不清楚甚至弄错了,则依据这些经典进行的其他研究,则从基础就失去了依据,其研究结果必然是不可信的。而文字、音韵、训诂三者本来就是合为一体的,必须统一地进行研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序”时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说文解字》,一般人认为是以字形为主的书,所以后人都称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字典,因此一般人认为研究《说文》属于文字学的研究。但王念孙不这样理解,他说段氏研究《说文》,是以文字为中心而兼具了声音、训诂之学,而不仅仅是研究文字的。
段氏研究《说文》之初,首先研究了古代文字的音韵系统,确立了《六书音韵表》,把古代文字的音韵分为十七部,以综该古文字的音韵,王念孙说他“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从而使古文字的“声音之道大明”。然后根据十七部的远近分合来分析古代文字的形声、读若之关系,以及文字的正义、假借义之关系,再“揆诸经义,例以本书”,从而使“训诂之道大明”。这样研究《说文》,就不是单纯的文字之学,而是把声音、训诂与文字整合为一之学,因此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而经学明”。王、段都是乾嘉学派的大师,他们把文字、音韵、训诂合三为一,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小学明,而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经学明。王念孙讽刺那些所谓单纯研究文字学的人,只知“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而於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这样的文字学研究,“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其学问的层次与视文字、音韵、训诂合三为一的整体性的小学相比,其深浅之相去何异于天壤。
同样,王念孙有《广雅疏证》之作,素被视为古代训诂学之名著,但段玉裁则不这样看,他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3]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其注之精粹,再有子雲必能知之。”以为能将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统一起来,才是最高明的小学。
[1] 《国学讲习会略说》,东方出版社《章太炎讲国学》,2007年版第9页。
[2]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以下简称黄侃《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3] 指王念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