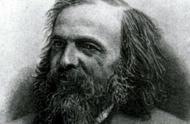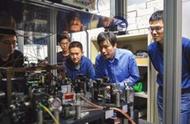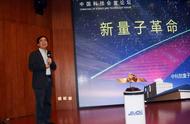据海森堡后来回忆,在索尔维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往往在吃早饭时告诉玻尔等人他夜里想出来的新思想实验。
而玻尔则开启“守门员”的防守模式,立即开始分析,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说明,到会上再详细讨论。
结果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玻尔就能给爱因斯坦证明,他的实验是驳不倒测不准关系的。
爱因斯坦则会在第二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实验,比前一个更复杂。
就这样循环往复,谁也不服谁。

此后,两人还开启过一次论文与论文的交流,把论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1935年,爱因斯坦、波道尔斯基和罗森三人联名,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全的吗?》(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简称EPR)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理论完备性的必要条件:物理实在的每个要素都必须在物理理论中有它的对应。即,如果不对一个物理体系进行干扰,我们就能确定地预测一个物理量的值。还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史称“EPR佯谬”。
五个月后,作为回应,玻尔专门写了一篇同名论文发表在同一杂志上予以答辩。
他以测量仪器与客体实在的不可分性为理由,否定了EPR论证的前提———物理实在的认识论判据,从而否定了EPR实验的悖论性质。
不过,就像EPR论证未被玻尔接受,同样玻尔的反驳也不能令爱因斯坦信服。
此后,两人之争也一直持续着。

直到1962年,就在玻尔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黑板上画了当年爱因斯坦光箱实验的草图,解释给前来的采访者听,这幅图也成了玻尔留下的最后手迹。
而这场持续十几年的争论也逐渐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科学史家马克斯·雅默曾评价,这是一场物理学史上的伟大论战,也许只有18世纪初的牛顿—莱布尼茨论战才能与之比拟。
One More Thing值得一提的是,玻尔的孩子们似乎也继承到了玻尔的物理和运动天赋。
他的第四个儿子奥格继承了玻尔的衣钵研究物理,并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4对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父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