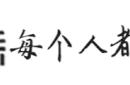此时,鲁迅早已经名满全国,是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泰斗,梁实秋不敢造次,只好忍气吞声。没想到,一个月后,鲁迅再次写出《拟豫言》,再次将梁实秋从上到下嘲弄了一番。
沉不住气的梁实秋终于站了出来并开始反击鲁迅。然而,鲁迅是久经沙场的战士,是疾恶如仇的思想家,岂是梁实秋所能抗衡的,梁实秋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开始意气用事,指责鲁迅的性格,说他对这样也不满,对那样也不满,但又没有解决的办法。他说鲁迅经常指责别人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显然,梁实秋关非善茬,他指责鲁迅的出发点,政治因素颇多。鲁迅因为自己疾恶如仇的性格,不仅不容于北洋政府,也不容于国民政府,甚至一度遭到通缉。

*人诛心,梁实秋明白这个道理,对他而言,无论是谁当政,他都能游刃有余地维护自己“贵族士大夫”的地位,但一直作为批评者的鲁迅做不到这点,只要自己足够阴险,也许就能祸水东引,置鲁迅于死地,再不济也要把鲁迅吓住。
但他忽略了鲁迅罕逢对手的寂寞和追求真理的决心,鲁迅看到他的文章后,认为终于遇到了一位像样的对手,很快便写出了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文章里,鲁迅不仅驳斥了梁实秋说自己“不满于现状”的说法,也对梁实秋“精神贵族”的倾向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
如果文学不能做到针砭时弊,那文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鲁迅一直坚持的理念。但梁实秋作为精神贵族的代表人物,不是靠写些小资情调文章供自己自娱自乐,就是为当政者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获得功名利䘵,他是想不明白文学存在的真正意义的。

胡适与梁实秋
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本就需要敢于站出来指出问题所在的猛士,鲁迅怀着一腔热血,不惧当时政府的迫害,捅破了这扇窗子,不惧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反观梁实秋,干脆躲了起来,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舞文弄墨,坐实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对他而言是很安全,但未免显得有些自私,甚至是媚上。
梁实秋显然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两人的论战,也吸引了其它人的加入。创造社的冯乃超看不惯梁实秋的为人,直接讽刺他为资本家的走狗。

冯乃超
梁实秋见状,立即发挥自己的长处,说鲁迅是赤色分子,梁实秋撰文强调: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梁实秋这话看似俏皮,实际包藏祸心,他直接将鲁迅归类为赤色分子,因为他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对所谓的“赤色分子”采取赶尽*绝的方针,如此一来,鲁迅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鲁迅当然看出了梁实秋的阴险,但鲁迅浑然不惧。据说,鲁迅在看守梁实秋的文章后,先是冷冷一笑,接着说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
鲁迅伏在案上,奋笔疾书,一篇经典的反驳文章横空而出,这就是后世有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