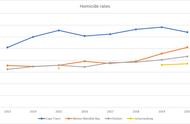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可可西里遇难女孩:远离城市的死亡》,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一个24岁的女孩在可可西里结束了她的生命,救援队员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她去往无人区的目的就是为了轻生。“可可西里”“文青”“飞行员”的标签为她的死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信息如此通畅的今天,我们理解一个女孩的死亡却并没有更容易。
记者/张洁琼

(插图 老牛)
无人区救援
8月11日晚上10点,海西州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长谢文淋回到家,将身上的蓝色制服慢慢剥下,接着走进了浴室。他今年44岁,业余活动比工作还令他感到疲惫,三年来,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高原上做救援,感觉自己的心脏和肺都不如同龄人的健康。这天,海西州乌兰县察汗诺地区的天空刚露出微光时,他和救援队的队员就开车到了格尔木戈壁,在山野中行进了6个多小时后,一名队员在一个山坡北麓的大石头旁发现了他们所要救援的那名修桥工人。在距离山顶200多米的一处山缝,修桥工人斜靠着一块大石头,一只手耷拉在上面,面容安详,谢文淋上前确认了好几次,“人已经走了,拍照做好坐标,等警察来吧!”
谢文淋根据现场状况拼凑出了修桥工人生前挣扎的画面:他抱着挑战自我的信心爬上了山,在翻越第三座时,两三米高的花岗岩挡住了他的去路,每向前走一步就像要翻越一道墙。爬至山顶时,他甚至扔掉了来时带的编织袋,里面装着能救命的雨衣、毛衫、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鸡蛋。他体力完全透支了,他找到一处山缝,停下来,打电话向家人求救。于是,8月9日凌晨,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值班员接到了这位工人家人的求助电话。“每次搜救,我沿着遇难者的轨迹走过,都会想到这些,有的死者手里有土,那是他生前想刨开一个坑,躲进去,就跟动物一样。太可怜了!”谢文淋告诉本刊记者。
他也见过没有半点挣扎痕迹的遇难现场,比如半个月前的那次搜救。他和10位救援队员,以及格尔木100多个警员一起,在可可西里高原搜寻了4天。7月31日,他们在戈壁上发现一件破碎的黑色外套、一条牛仔裤、身份证、学生证和一具遗骸,这些全部属于一个24岁的女孩,谢文淋管她叫小黄,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黄雨蒙。从7月末开始,媒体、网民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她身上,各种标签打在她身上——一个在可可西里离奇失联的女大学生,一个被诗和远方蒙蔽了的无知文青,一个向往自由的女飞行员……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黄雨蒙在7月7日4时到达了格尔木,早上8点,她坐出租车从格尔木市黄河大酒店朝G109国道出发,中午12点到达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后,她让出租车司机返回市区,自己一个人背着行李向可可西里继续深入。下午3点,她来到了索南达杰保护站附近的清水河区域。第二天,7月9日18时,她的手机关机,彻底失去消息。
谢文淋第一次接到小黄家属的求助电话是7月26日晚,是小黄的闺密方薇薇打来的,他解释说因为黄雨蒙父亲不善言辞,所以跟救援队、媒体联系的都是方薇薇。方薇薇告诉谢文淋,小黄失联已经超过20天,7月9日小黄的父母就报了警,至今没有音信。谢文淋脑袋一沉,心想:“在无人区失联20多天,可能连一件遗物都找不到了。”但隔着电话,他没直说。
27日凌晨,谢文淋和其他10名救援队队员载着头盔、救援服、药品和氧气瓶,开车驶进清水河区域。谢文淋所在的救援队有接近60位成员,每次出任务,他们会分成两支队伍,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轮换着来。这次搜救,格尔木派出了100多名公安干警,这么大的阵仗也是谢文淋头一次见到。警员和救援队员们被分成十几个组,每个人间隔二三十米,有顺序地在戈壁滩上排开,以差不多的节奏一起沿着河向前挪动。搜救那几天,谢文淋每天睡觉的地点都不一样。第一天是在车上,第二天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板房里,第三天,他跟队友就地支了一顶帐篷,裹着睡袋过了一晚。
7月的可可西里温度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保护区里的藏羚羊开始迁徙,花会迎来一段短暂的开放期,植被低伏在沙土表层,戈壁也显得没那么荒凉。但即便如此,天气对人的考验还是不可小觑。“我从小在这边长大,没有听说过冬天把人冻死的,都是在夏天。”谢文淋告诉本刊记者,“冬天穿得厚,下雪了,刨个雪坑也可以。最怕的是(夏天)下雨,一下雨就把人淋湿了,接着急速降温一下雪,就会失温。”失温症是指人的大脑、心肺等核心生命器官的温度低于正常温度,从而造成死亡的病症。在户外,气温低是导致人患上失温症的重要原因,但温度不低的环境中,湿度过高或风力过大,同样也会导致失温症。在谢文淋看来,大部分闯进可可西里的游客都对当地的极端环境缺少认识。“因为现在咱们对外的一些(关于可可西里的)宣传,这里从照片上看到的永远是美的,像拍电影一样。但现实是你到了这里,可能有高原反应,可能失温,很恐怖的。”
一提到网络媒体上呈现的可可西里的形象,谢文淋就加重声音,他改用一种说教的语气告诉我:“我希望你们这篇文章的作用是警示那些人,他们对这儿有美好的想象,保留它就好了,别真来。”
死亡之谜
7月30日晚7时,格尔木警方在可可西里清水河流域南侧发现了人体骨骼,两天后,经过DNA检测,确定为黄雨蒙的遗骸。警方在随后的通报中表示:“经初步侦查,排除他*。”谢文淋根据多年的经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见过小黄的遗物,那是一个双肩包,包的正面绣着一个老虎头。“她的双肩包上、衣服上都没有血迹,应该就是失温或高反导致的(死亡)。”至于骸骨被分解,他认为是尸体冻僵以后被野生动物咬食所致。
“有没有可能是还活着的时候,遇到了猛兽攻击?”我问。
“可能性非常小,野生动物有它们自己熟悉的生物链,我们这几年生态区保护得很好,不存在食物不足的情况,所以它没必要去冒险(攻击人)。”谢文淋说,“要么是那种正处在发情期的雄性野兽,要么是野牛,它觉得你闯进了它的领地,除此以外,动物不会主动攻击人。”
发现骸骨以后,每天不停响起的电话让谢文淋不胜其扰,有的是他许久不联系的朋友,有的是不知姓名的陌生人。他接起电话,对方的第一句都是:“那个可可西里失联的女孩是怎么死的呀?”有时他会直接挂断,有时他会勉强讲两句,但从不直白地说,只是不住叹息:“这么好的女孩子,怎么就想不开呢?”
“她当时已经没有求生的*了。”谢文淋告诉我,“小黄遇难的地方距离清水河不远,河道很深,完全可以避风避雨,遇到极端天气,求生的本能就会把她带过去,除非……”此外,他对小黄因为延期毕业而心情郁闷的情况也有所耳闻,还有黄雨蒙包里的半瓶矿泉水以及一小瓶安眠药(也有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遇难现场发现的只是有安定成分的药品)。以上种种让谢文淋推定,小黄去可可西里是放弃了希望,吞了安眠药以后昏睡过去,失温而死。
但并非所有人认同谢文淋的推测。“她要真想死,为什么去可可西里还要跟出租车司机砍价呢?为什么还说买了纪念品要回去送人呢?”最先对黄雨蒙失联进行报道,帮助她的家人寻人的西宁记者金华山对我说,“所以格尔木警方给出的结论是她对可可西里的环境预估不足,遭遇了意外,这个结论她父母也是接受的。”
8月4日,黄雨蒙的父母在可可西里为她办了天葬。“她喜欢那里,我们就把她留在了那里。”电话中,黄父声音疲惫,他连夜乘火车到了西宁,又搭飞机飞回了绵阳。“我和她妈妈想静一静,这一个月来,我们实在是心力交瘁,我们不想去想这些事了。”他说。
飞行员
2015年,黄雨蒙考入安徽理工大学,专业是药学,她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大热情,反倒是经常跟朋友提起,自己想当飞行员。那一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了安徽理工大学招飞,她填了报名表,经过视力检查等一系列身体素质检查以及面试后,如愿入选。她当时的好友郭倩倩记得,学校参加招飞的学生有近百人,最后被录取的也就五个。
郭倩倩说,黄雨蒙的性格“一直很阳光,很勇敢,就像小鸟一样,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有一次,她主动约郭倩倩去山东日照旅游,两人报了一个旅行团,在日照玩了两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边。那是黄雨蒙第一次看到大海,她满脸都是兴奋,对每一个娱乐项目都充满了好奇。白色的摩托艇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水痕,轰轰的声音在水面上来回晃动,黄雨蒙便蠢蠢欲动了,她告诉郭倩倩,来一次太难得了,一起坐一次吧。她手里的钱不够,便管郭倩倩借钱去坐。
那次尝试对郭倩倩来说,实在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摩托艇的每一个急转弯都让她胆战心惊,她的手紧扣着旁边的板子,20分钟都不曾放松。“但雨蒙就是很开心,很享受,还在上面自拍,完了还要求再转一圈儿。”郭倩倩说,“她确实是很勇敢,胆子很大。”
2017年,黄雨蒙转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行技术班,加上她,班里一共有6名女生。在南航上了一年的专业课后,2018年8月,黄雨蒙跟其他50名同学一起前往南非艾维国际飞行学院试训。艾维航校位于西开普省,西开普横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西南处正是著名的好望角和开普敦,那是南非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和黄雨蒙一起试训的学员王骏告诉我,他们在南非学习的所有费用都由航空公司负责,此外,航空公司还会每个月给他们七八百兰特的生活费,折合人民币约400元。学员们有10门理论课和25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只有全部完成并通过考试,才能拿到国际商用飞行员执照。训练有五个阶段:单飞阶段、私照阶段、商照阶段、仪表阶段、高性能阶段。其中单飞阶段是最基础,也很困难的阶段,考验飞行员独自驾驭飞机的能力,学员要在教员的陪同下,至少完成包括起飞、降落在内的三次完整飞行,才会通过考核。每一阶段都有训练时间限制,超出时间仍旧达不到教员标准的,学员就不得不退出。黄雨蒙就是单飞阶段训练时间超过35小时,所以未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有不懂的地方就会说,可能是一点点小事,她也会跟教员说,教员又不能很好地理解她,以为她是害怕。”王骏分析道,“我们每个人单独飞行的时间都不一样,教员给她安排的课程不是很紧凑,她自己拖得也有点后了,教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其实她的技术水平是在中等的,(正常通过)应该没问题。”
王骏记得,2019年初的一天,黄雨蒙最后一次试飞。如果这次试飞检查员还不同意她单飞的话,黄雨蒙的训练就将终止了。那天,训练基地的所有同学都去了航校机场为她加油。王骏盯着黄雨蒙走上飞机,心里也为她捏了一把汗。在天空飞了一圈,飞机落地后,黄雨蒙和检查员却没有立刻走下来。“一般都是飞完直接下来,然后去教室里做讲评,而且一般放单飞的话,不会中途停下来重新打火,她飞的时候中途停了两次。”王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想到,黄雨蒙走出机舱的第一反应是冲他们竖起了拇指。“她还在冲我们笑,但那个笑容就是她自己挤出来的。”王骏说。
黄雨蒙没能通过单飞检测,2019年3月,她离开南非,一个人返回南京。临走前,同批次的其他五个女飞行员都去机场为她送行,但黄雨蒙的飞行员梦想暂时中断了。事实上,南航并非每年都会招收女飞行员,由于高度依赖航空公司的用人需求,2018年以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取消了招收女飞行员的项目,从2010年第一批女飞行员入校,这一项目仅仅存在了8年。
回到南航后,经过学校面试,她转入了空中交通管理专业,这一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出路就是做地勤。留在南非试训的王骏不时还会接到黄雨蒙的*“骏骏最近又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吗?”她喜欢看南非的天空,便让王骏拍下照片发给她。有一次,她跟王骏提起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说虽然进不了民航了,但她还想去通航。通航可以开直升机,做山区营救或喷洒农药。
今年6月23日,王骏在微信上跟黄雨蒙聊天,听她说空管专业有一门课需要重修,要延期毕业了。当时由于疫情,王骏被困在南非,无法回国也无法毕业,便开玩笑说:“等我回去,我们一起毕业。”黄雨蒙回了一个“好呀”的表情。“我以为延期毕业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说完,王骏沉默了一会儿。
有关自*的讨论
从7月末黄雨蒙失联的新闻出现到8月1日发现遗骸,网上掀起了对她死亡的讨论热潮。有人评价她是“喝了毒鸡汤的无知文青”,也有的舆论认为她“抗压能力不够强”,“不考虑父母家人的感受”,自私、任性。由于格尔木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寻找,黄雨蒙之死也引发了“浪费公共资源”的争议。但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理解一个城市女孩去往荒野的死亡?
她看起来不属于传统自*高发群体中的一员,似乎也难以找到传统对应的解释方法。过去农村自*事件频发时,我们会讨论城乡差距和乡村的衰败,妇女自*率的剧增则指向了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少年儿童的自*可能会和学校和家庭教育建立联系。但如何理解青年大学生对生命的态度,我们的归因只剩下了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弱、不负责任等。当8月份从新闻上看到好友因为延期毕业而选择自*的时候,王骏先是不相信,接着又陷入极度的内疚,“是我不够了解她吗?还是我没有感受到她的痛苦?”这种悲痛后来转化成了一种愤怒,他抱着手机一条条回复网络上那些指责好友的人。他不理解,为什么网友们这么热衷于指责一个人的死亡。他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仅仅用自私、任性来评价她。
19世纪时,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就提出,死亡,尤其是自*,是和社会整合度高度相关的。过高或者过低的社会整合、过于混乱或者过于严苛的社会规则,都会导致自*率的上升。而加拿大医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费立鹏早年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在中国,自*并不主要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黄雨蒙勇敢、乐观的外表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伤痕,这些伤痕背后又牵连着什么社会肌理,我们已经很难追寻。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也无法让死亡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选择。对还活在世上的亲人来说,生命仍然是最好的慰藉,死亡仍然是最沉重的打击。
在黄雨蒙确认遇难的半个月后,她的爷爷奶奶仍不知情。有一天,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黄爷爷,战战兢兢地试探道:“雨蒙有消息了吗?”
“还在找。”黄爷爷说。我听到电话那头有微弱的哭声。
“谢谢你们关心我孙女,她爸爸还在找。”他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