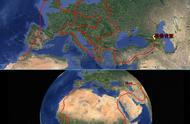黄哲

“他这个人啊,就是碗乌冬面!”在日语语境下,乌冬面怎么就成了“早鸟”的代名词?原来,日本的乌冬面馆和正宗的苏州面馆一样,通常是清晨开门,过午卖完不候。
不过,一部《深夜食堂》让全世界都知道,炒乌冬在星月相伴下更加美味。原因在于,只要下油锅的,在日本都算菜,和他们的饺子要就米饭吃一个道理。
饺子和拉面,都是二十世纪才出现在日本餐桌的晚辈后生,乌冬面作为上千年的老人家,“早睡早起上早班”,实在再合理不过。
众所周知,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地球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变冷变干。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南下寻找生存空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史之乱。
盛唐气象从此一去不复返的同时,辽阔的大唐疆域从北向南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面进米退”。
彼时,不知是不是在登陆福州时受了当地一碗面恩泽的缘故,日本高僧空海东归不仅带回了佛法和汉学,还让他饥贫的家乡赞岐(今香川县)变成了日本粮仓,并因当年他吃过的那碗面而闻名于后世。

在遣唐高僧空海大师的故乡善通寺市,面馆纷纷以汉字“饂饨”而不是日语拼音为名,也昭示着这种古老食物和中国的关系。本文图均为 黄哲 摄
碗里没有一滴油,却被人奉为信仰
“恭喜你运气好啊。”作为整艘轮船的CFO(首席食物官),欧巴桑一边听我和她抱怨赶这班轮船的一波三折,一边熟练地三下五除二,下锅、过水、浇高汤、摆油豆腐、撒裙带菜和葱花,没等我抱怨完,一碗新鲜出锅的乌冬面就堵住了我的嘴。
习惯了“日本铁路=美味便当”,我想试一下船上美食又如何,于是,从本州到四国的跨海之旅,我没有选择火车或大巴,而是一班几小时的轮渡前往香川县首府高松。
轮船上,其他零食和饮料屈身自动出售机,唯独一座先煮现卖的面档,占据了指挥室正下方,整个客舱的中央C位,恐怕就是对民以食为天的最好说明。
热汤热面,最能抚慰辘辘饥肠。更何况这乌冬面的粗大程度,恐怕只有兰州拉面家族里的二柱子可比。比起拉面,它水分更少,自然也更实在也更经扛。牙齿嚼碎它时,有点像吃海鲜里的软体一族,面身仿佛也有求生欲一般,不停反弹和挣扎。再喝口汤,清淡鲜美,油豆腐口感清甜,汤里却连半点油星都看不到。

前往乌冬面故乡香川县,轮船上现做的一碗狐乌冬,虽然简单,却因新鲜手打,是“下车面”的极品。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油豆腐颜色质地如狐狸毛色、又是传说中狐狸爱偷吃之物,这一平民版配置也被称为“狐乌冬”。
“你要是坐了前面两班,就只能吃冰箱里拿出来的半生面啦。”大妈操着浓重的香川口音,“只有我们这班从高松出发前,刚好赶上今早‘制面所’新鲜出来的生面。”
香川县人口和经济都在日本倒数,唯独小麦消费量在全日本一枝独秀,比第二位高了一倍以上。而答案,就在那块“欢迎来到乌冬面的故乡”的牌子上。在香川各地,它无处不在。
乌冬面故乡的人们,除非实在不得已,一般都会拒绝机器产品和冷藏成品,只接受当日新鲜手打的乌冬面。在日本版的各种地域歧视梗中,香川被外地人认为是“乌冬面脑袋”,而香川人看外地则是,“他们真可怜,不能天天吃到好吃的乌冬面”。
制面所,到现在也是骄傲的支柱产业
欧巴桑说“制面所”时,我起初吓了一跳。不知是她口音太重还是我听力太差。因为日语里的洗脸池叫“洗面所”,发音与之相似。就算日本水龙头出来的也可直饮,您也太不避讳了……
后来,我在脑海里搜寻高松好吃去处时,想起来《孤独的美食家》里,五郎叔曾经在寒冬里为乌冬面早早排队的情节,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制面所!
在日语汉字中,制x所就是制造某项产品的小工厂甚至作坊。但能冠以此名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仅负责生产,还要有研发功能,往往少不了专利傍身。
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靠的就是这无数家如毛细血管般,同时解决税收和就业,甚至还引发不少技术革命的小微企业。
查了这家松下制面所的营业时间,我决定当天早早休息,翌日起大早,先吃第一锅手打乌冬,再逛旁边米其林三星级景点栗林公园。
一条小巷深处,前店后厂,其中前店又分两开间,一间只有寥寥几个凳子,周转率之高远胜流水席,一间则只能对着窄窄的台面站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