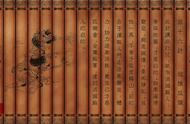□张一芳
渊薮久远的玉环海鲜饮食文化
玉环地处海岛,旧属“扬州之域”,瓯越之地,沿海鱼贝资源丰饶,海鲜饮食文化渊源久远。从三合潭遗址出土文物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越绝书》称越人“劗发纹身,蝉食蛇蛤。”海产品在先民餐食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而从同一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陶制网坠、青铜鱼钩和鱼刺,先进渔捕工具的使用,证实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开始走向海洋,从岸滩捡拾转而进入近海网捕。并且,当地出土的新石器晚期三夹式石犁铧,其意义还在于为研究早期的海洋农耕渔猎文化和海岛先民的生存状态提供证据。这与司马迁《史记·贷殖列传》所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随赢蛤(食螺蛤)……”是相吻合的。
火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膳食质量,更在于推进进化。美国烹饪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说:“烹饪法是最早的化学形式,烹饪的革命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当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时,中国人就已经进入了熟食文明。三合潭遗址杆栏式住居中的灶具、陶制器皿,和东青山晋代墓葬遗址的炊具和食器的发现,以及对灰炭层陈迹和大量经加工的动物遗骸的探究,足可见海岛先民的烹饪技艺之高,食之讲究与精良。
海盐是最早进入食系的调味品。“鳣鮪之醢,大夏之盐。”《吕氏春秋·本味篇》也为海鲜的腌渍腌晒、贮藏转运提供了条件。史称:黄帝时即“煎成盐。”(《世本纪》)玉环的海盐或许可以上溯到很久远。至唐宋,玉环即有官办盐场,曰密莺,曰天富北监,并设有盐官,领知监衔。宋代名臣王十朋有《送凌知监赴任玉环》诗,《梅溪集》按:“天富北监,在玉环。”盐在当时属于国家控制物资,与铁居同等地位。

三合潭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鱼钩

三合潭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鱼刺
东晋谢灵运来到“东带海采门”,写下“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谢灵运的《游赤石进帆海》可能是目前看到的最早有关玉环舟船离岸渔捕和海面作业的文字。著名训诂学家孙诒让考证称:“海采门即指:楚门、横坎门、大门一带海域。”
北宋左司员外郎倪涛,因在宋徽宗大观六年(1124)谏阻攻打辽国,遭追*,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携子孙辗转徙玉环,隐居倪岙。“十年天涯秋,摇落几芳菲。马蹄岁月去,梦蜨东南飞。平生丘壑志,有音辄乖违。不如孤征鸿,春风自知归。”正是避世隐居的真实写照。倪岙又作渔岙(读音仍为“ni”)。此处依山面海,砟柴搭灶煮海鲜,自是官场风险无法比之。
元代诗人李仕兴到玉环,看到的是傍海渔村的美好画卷。“海天日暖鱼堪钓,潮浦船回酒可赊;傍水人家无十室,九恁舟楫作生涯。”(元·李仕兴《抵楚门》)到了元末,东南沿海诸如方国珍反元降元、周嗣德与方汝宾(方国珍侄)争斗等乱象,肯定对民众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破坏生产进而涂炭民生。诗人陈高避居玉环,眼见的是“竝海居人不种田,捕鱼换米度经年;钓船渔网都狼籍,老稺流离哭向天。”(元·陈高《不系舟渔集》)
明嘉靖十八年(1539),朝廷因倭寇扰边,徙民于内地。但随着航海和远洋渔业的发展,闽、粤渔民云集而来,或搭寮定居,或作季节性往返,披山渔场先于舟山成为当时渔捕的最佳海域,钓艚岙(俗称大坎门)因惠安大钓船专门停泊而得名。崇武诗人黄克晦“击楫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明·黄克晦《崇武乍山草庵得家字》)把坎门钓捕渔业和海产带鱼堪比闻名东南亚的台湾彰化米。
清雍正六年展复建置玉环厅,招徕邻近六县民众,闽、粤渔民也得以结保定居,农、工、渔、盐各业,在相关适当宽松政策的激励下,稳步发展。渔业生产成为地域的主导产业。我们还可以从清玉环厅同知陆玉书的“闽樯越舶来多少,都为鱼盐习坎喧。”(清·陆玉书《钓艚岙》)看到当时渔业的延续、传承和发展。
同样赞叹当时渔业生产景况的诗文,还可以读到的有:戴湘云“万顷洪涛随日上,一行巨舰倚云开。”(清·戴湘云《灵门山观潮》);郭钟岳“不讨崖头整钓船,收风欢喜得海鲜,朝朝暮暮潮头弄,万顷碧波海作田。”(清·郭钟岳《海作田》);陈春晖“利薮江淘蛤,生涯海种蚶。泽人无穑事,手足也涂沾。”(清·陈春晖《玉环杂咏》)等等。清光绪六年《玉环厅志·卷之一·下·物产篇》介绍玉环海产“鱼之属”有:鲈鱼、黄花鱼、鲳鱼、鳓鱼、鲻鱼、鲊鱼、乌贼、章巨、望潮等31种属;“介之属”有:蛏、蛤、蚶、蛎、螺、蝤蛑、虾、蟹、沙蒜、淡菜、鲎、蜐等22种属。

我们在领会渔业生产的发达带来丰富海产的同时,仿佛在同时体验特产海鲜的丰腻美味。陆玉书“海岛孤悬别有天村,潮来潮去水当门;一家老少都张网,网得鱼虾作饭餮。”(清·陆玉书《环山杂咏》);王咏霓:“大鹿小鹿遥相对,黄门坎门风信长;网得鱼虾都成对,妒他眠起不分将。”(清·王咏霓《玉环杂咏》)所述的是多么其乐融融的渔家生活呵!并且海鲜贸易也相对发达,除渔行的大宗交易外,“行贩”和“担鲜”扩展了海产流通,“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来;黄鱼白鲞同虾蟹,都把樵苏换得回。”(清·陆玉书《西青街》) “不问寅与巳,鱼鳞匝地摊;冯罐如客此,剑铗不须弹。”(清·张英风《中街鱼市》)。并且,民间还存在大量四时海产和适时取食的谚语。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丰富海产,既是民众生活的物质保障,也是海鲜食尚形成的资源支撑。
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世代因承的民间生活中,看到时产海鲜是如何渗透到传统习惯和礼仪俗尚等精神层面的活动中,诸如节时馈赠、拜师收徒、定亲纳聘、生诞寿贺、惯和礼仪俗尚等精神层面的活动中,诸如节时馈赠、拜师收徒、定亲纳聘、生诞寿贺、乔迁踏福甚至祭祀礼拜,无论作为礼品、宴品,甚至供品、祭品,几乎无一能与时鲜海产割断关联,其中,因为品名谐音而衍生的吉祥寓意,为公众所乐道。
我这样闲扯八搭,抱定一个对接前人的企图,就是想看看海岛玉环的海鲜美食,究竟是如何的非同一般、如何的渊深久远、如何的富于蕴涵。
玉环的海鲜美食,其实是很民间的概念
很多人都听说过玉环海鲜的美名,本地人也时不时地发出“到玉环来吃海鲜”的邀请,来到玉环之后,面对鳞次栉比、霓虹满目的酒楼餐馆,却晕了头。到底玉环有没有一种食品是正宗的传统、能够彻头彻尾代表玉环特色?本地媒体、百姓、官员也一再为这个问题挠头,网上投票以及各种评议评比等等,都在忙乎。并且,一说起“到玉环来吃海鲜”,能让我们想起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
在我看来,所谓“到玉环来吃海鲜”,并不是说玉环的哪家店或哪个菜式好吃,更不是说玉环的哪条街集中了全岛全县的美食精选——尽管这也是玉环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当然,一个以岛县著称的海鲜饮食是不可能没有历史沉淀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挖空心思地去界定或者寻找它的代表作。所谓代表作,其实就是品牌了。所谓品牌,一是要本地外地都公认;二是要有掌故来头有说道:三就是有册封认可之类的手续。如果像北京那样,虽无满城美食,一只烤鸭足够;或如重庆,一盆火锅名誉天下,那该是何等省事!
不过我要说的是,无论你想吃什么,只要是在玉环拿得上桌的,就总得带上一点点玉环的味道。玉环的现有居民,大多是闽南和邻近六县移民的后裔,年代并不久远,大约是270多年,跟美国的移民开发史差不多年头。年代不久远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凭此才离本相近矣,否则就会显得模糊或生出太多变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