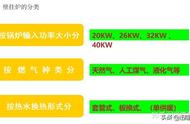登顶珠峰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高达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峰顶险象环生。即便是有资金保障,最好的装备、事前训练和人员协助,仍有可能在山顶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莫测的雪崩和难以预知的身体反应中遇险。珠峰究竟有什么魅力,“诱惑”一代又一代人去征服它?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的作者为登山家、作家马克·辛诺特(Mark Synnott),希望解开一个谜团,那就是在中国人登顶30多年前,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究竟有没有达到顶峰?为此,辛诺特在2019年春天投身于一场几乎没有希望成功的珠穆朗玛峰登山之旅。探险团队一路追寻到加德满都,再到青藏高原,一直到珠峰北坡,并陷入一场巨大的风暴……
这一年是“珠峰崩裂之年”,登山季来到时,大量登山者涌上珠峰,造成峰顶第二台阶顶部的“致命大堵车”,最终有11人在珠穆朗玛峰遇难。2019年5月30日,辛诺特经历了混乱和艰难,一度在死亡边缘游走,但之后如愿登顶,但他在下撤的路线上还是没有找到欧文和那架相机。以下内容选自《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美]马克·辛诺特 著,舍其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版。
那天上午,其他所有人离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只有咫尺之遥,而我坐在营地里,感觉自己就像搁家里赶作业的孩子,而好朋友们都在外面参加狂欢派对一样。山上所有人都在赌天气,而他们正在赢得这场豪赌。那一刻,这个登山季梦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很多都站在了地球上最高的地方,要不也是很快就会站上去。我们没有去,其实也是在赌。如果就这样了呢?如果这个登山季没有第二个窗口期呢?我们的大本营负责人达娃,那天早上对我们留下来等待的决定也颇有微词。
珠穆朗玛峰是一门生意,而生意的成败全看资产负债表。我们在山上每多待一天,就要多花达娃一天的钱,包括工资、食品、管理费、各项杂费等等。错过这个天气窗口,我们就浪费了喜马拉雅探险公司好几千美元。当然还有西藏登协,我们没完事儿他们也不能离开,而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开支和想法。毫无疑问,西藏登协的人也会很想早点回家跟家人团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还会允许我们在山上待多久。
这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跟杰米一起回顾了一下长期天气预报。情况不容乐观。所有人都管马克·德凯瑟做的叫“欧洲”珠峰天气预报,他和费金都认为,目前这个窗口正在关闭。现在预报的是,未来几天会有大风。他们认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登顶窗口期的概率是一半一半。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北坳现在会不会成为我们此行抵达的最高点,成了天意。
死亡地带并不是非黑即白
那天凌晨,一丝天光都还看不到的时候,45岁的奥地利商人莱茵哈德·格鲁布霍费尔(Reinhard Grubhofer)用尽全力爬上了第一台阶顶端一块光秃秃的岩石。站在这个海拔8560米的著名地标上,格鲁布霍费尔大口吸着氧气面罩里的氧气,花了一分钟才搞清楚自己在哪里。这时候飘着小雪,风也很小。按照天气预报,环境温度应该在-37℃左右。他往前看了看,山脊上是一长串头灯,就像圣诞彩灯一样。他估计自己看到的头灯有80个的样子,但实际上,在东北山脊上面这一段,这些穿成线的头灯的数目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他所在的登山队是最后离开突击营地的队伍之一,一直到夜里11点才动身。
在南边远处,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东南山脊上,他看到也有同样的一长串头灯。几百只小小的萤火虫排着队慢慢向地球的最高点行进,真是一个神奇的景象。但格鲁布霍费尔对自己看到的情景并没有觉得有多高兴,反而是深感不安。还在为攀登珠穆朗玛峰做准备时,他就经常做同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山上碰到了大堵车,堵在中间进退不得。而现在,这个噩梦可能正在变成现实。
他想起自己对妻子安吉丽卡(Angelika)和四岁女儿诺拉的承诺,他们对女儿的爱称是“小老鼠”。他曾和她们开玩笑说,他就像一只飞去来器,冒险结束之后总是会平平安安地飞回起点。他也曾告诉妻子,他了解自己的身体也知道自己的极限,如果到了出于谨慎考虑必须回头的关头,他会毫不犹豫转身返回。在他们位于维也纳的舒舒服服的小家里,这么说听起来非常理性也非常合理,但现在,在东北山脊上他意识到,在死亡地带这么高的地方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好多不同灰度的灰色重叠在一起。
给他提供登山服务的是一位传奇人物,名叫卡里·科布勒(Kari Kobler)的瑞士向导。他告诉这支队伍,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在日出时登顶,这样能留给他们12个小时以上的白昼时间用来下山。但也有一些机动的余地。他把关门时间定在上午10点,到这个点无论爬到了什么地方,就算离顶峰只有30米,也必须掉头往下走,不能有任何质疑。11个小时本来无论如何都够登顶了,但这人山人海的样子让一切都慢了下来。格鲁布霍费尔在第一台阶底部就等了将近半小时。还有240米的高差,在曙光初现前登顶已经不可能了,而现在就连能不能在关门时间之内登顶看起来都不能确定。我能做到吗?他问自己。有一阵他抬头往上看,仍然满怀希望。好的,这么做可以的。打起精神,莱茵哈德。你做得很好。我们继续前进,登上该死的顶峰!但随后又有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在干吗?花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你该掉头往下走了。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听到冰爪在岩石上刮擦的声音,他转过身来,看到恩斯特·兰德格拉夫(Ernst Landgraf)也无比艰难地翻上了这个台阶。兰德格拉夫跟他住同一个帐篷,也同样来自奥地利,生活在奥地利东南部施蒂利亚州(Styria)的一个小镇,这个乡村地区以农业和多山而闻名。兰德格拉夫的德语方言口音特别重,格鲁布霍费尔生活的地方离首都只有几小时车程的,有时候很难听懂兰德格拉夫说话。兰德格拉夫有家室,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和野外滑雪运动员,已经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他以前在建筑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而且颇有建树,两周前他退休了,随后便启程来到了珠穆朗玛峰。跟很多有志于加入“七大洲最高峰”俱乐部的人一样,兰德格拉夫也有意把最难的这座山留到了最后。
兰德格拉夫悄无声息地走上来时,格鲁布霍费尔觉得,这位奥地利同胞能走到这么高的地方,已经相当了不起了。这次登山从一开始,兰德格拉夫就一直头痛得非常厉害,因此还在大本营的时候科布勒就让他吸着氧睡觉。他们开始一轮轮上山适应的时候,兰德格拉夫总是落在后面。在用餐帐篷里,他对自己适应起来有多艰难直言不讳,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考虑就此放弃。
格鲁布霍费尔很喜欢兰德格拉夫,而因为他俩都是奥地利人,他们队伍一路过来住酒店时,科布勒总让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彼此都很友好,两人之间也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分歧或紧张局面,但确实让格鲁布霍费尔有点儿恼火的是,兰德格拉夫似乎并没有为这次登山刻苦训练。兰德格拉夫说,那个冬天和春天他一直辗转阿尔卑斯山各地滑雪,但并没有严格按照科布勒为所有客户制订的训练方案去训练。因此,兰德格拉夫不仅是这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也是体能状态最差的。既然一支登山队的实力由其中最弱的成员决定,人们很难不因为兰德格拉夫没有做更充分的准备而感到有点恼火。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着实有些奇怪。到要去冲顶的时候,兰德格拉夫突然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前一天,他们俩差不多同一时间从2号营地(7790米)出发前往3号营地(8300米),珠穆朗玛峰的向导们早就从多年经验中知道,对大部分登山者来说,这都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表现很好的人会有很大机会登顶,表现不怎么样的第二天可能就得往下走了,而不是继续往上。格鲁布霍费尔这一天过得很糟糕,可能有部分原因是他的氧气面罩跟他棱角分明的面部特征不大匹配。面罩总是滑到他下巴上,他从来没觉得这个面罩在他脸上严丝合缝过。早先兰德格拉夫走在前面,这一天里他也一直在跟大家拉开距离。登顶这一天他又冒了出来,看起来强壮得很。看到朋友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正是格鲁布霍费尔现在需要的动力。他转向山顶,跟自己保证说,到第二台阶的时候他会重新评估。
他一定是落在了后面,
自己的氧气也用光了
格鲁布霍费尔看到的他前面的灯光,有一束属于印度素食主义登山者昆塔尔·乔伊舍尔。乔伊舍尔来到第二台阶底部的时候,也开始对此行产生疑问。他是这天晚上最早一批从突击营地出发冲顶的人之一,他的夏尔巴协作名叫明玛旦增(Mingma Tenzi),他俩属于另一支更大的登山队,不过他们比其他人先出发,因为想着走在队伍前面肯定比在后面要好。他们俩多年来一直都一起登山,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或一支两个人的队伍,而不是六个人或八个人的队伍,那么比你慢的队伍会更有可能让你超过去。
快速超车是成功登上大受欢迎的8000米级山峰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他们越来越接近走得比较慢的登山者的时候,明玛会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上调到4。这样一来乔伊舍尔就能快速接近他们,表现出身轻如燕的样子,而大部分人也会很乐意让他们超过去。超车需要暂时从路绳上解开,所以把握好他们的速度和时间也很重要,这样就可以在地形不那么险峻的地方超车。超过去并安全扣回到路绳上之后,明玛会马上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再调回去。(跟大部分夏尔巴登山者一样,明玛的氧气流速会设在1上面,而且这一天都会一直保持这个流速不变。)这个策略那天早上他们已经用了几次,效果也都很好,但有一支队伍他们没能成功超过去,那就是“超越冒险”登山队。第二台阶是整条路线上最困难的一段,现在他们就被困在了第二台阶的底部,前面是三个印度小孩,在梯子上乱动。
第二台阶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岩壁。这一段的高度总共有27米的样子,但分成了两层,中间有一段没那么陡的积雪路面。下面那段基本上就是一条之字形的坡道,没有上面那么陡。但当你尝试爬上去的时候,这一段的梯子会嘎吱作响,还会移位。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有个印度孩子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才能爬上这个摇摇晃晃的装置。乔伊舍尔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孩子踏上最底下一级横档,梯子移位了,那孩子的脚滑下来,整个身子也挂在了上升器连着的路绳上。另一个孩子在他上面一点,还有第三个孩子在下面等着。有三个夏尔巴人夹在他们中间,乔伊舍尔听到他们在朝那个孩子喊叫。这些孩子来自印度南方的部落地区,说一种叫做马拉地语(Marathi)的地方语言,但他们大多数都能听懂印地语(Hindi),这是印度的主要语言,夏尔巴人说的就是印地语。刚开始他们说的都是鼓励他的话,比如:“加油,你能做到的,你一直都爬得很好。”但那个孩子仍然在上面不得要领,局面便开始紧张起来。其中一个夏尔巴人冲他大喊,叫他麻溜的,这时在第二台阶下面已经开始形成小规模的交通堵塞。明玛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降到1,好让耽误的这一阵不会消耗太多氧气。堵着的人全都跺着脚,挥动着手臂,免得手脚冻僵了。
这样毫无希望地挣扎了半小时后,终于有两个夏尔巴人站到这孩子下方,从下面把他往上推,而上面另一个夏尔巴人一手抓住梯子,另一手往下够那孩子的背包带,就像机场的行李搬运工一样把那孩子拽上了上面的平台。
乔伊舍尔和明玛登上第二台阶后看到,这些印度孩子坐在一小块平地上,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胸脯上下起伏。明玛跟印度人的夏尔巴登山者讲了几句话,随后他们小心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三道台阶中,第三台阶是最简单的,只是一段大约6米高的岩壁。翻过这里之后,明玛和乔伊舍尔登上雪坡,后来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要经过这里向山顶进发。乔伊舍尔抬头看到,上面离他30米的地方有一盏头灯,那里有一段岩石横切,登顶路线在这里右转切入顶峰金字塔的北壁,这样就能避开一段陡峭的雪坡,而有人就在这道横切开始的地方休息。乔伊舍尔的头灯已经不亮了,但西边的天空挂着一枚亏凸月,在云层中时隐时现,雪地在渐渐减弱的月光下反射着光芒。天空时断时续地飘着小雪,雪花在乔伊舍尔的脸上打着旋。明玛走在前面,每走几步,他就会转过身,用头灯照亮他下面的斜坡,这样乔伊舍尔就能看到该往哪儿放脚。乔伊舍尔越过明玛向上看去,看到他们上面的那盏灯没动。
他们走上这片雪地顶端,发现一个夏尔巴人坐在一小段平台上,通过一团缠在一起的绳子挂在几个被砸进岩石裂缝的岩钉上。明玛用头灯照了照这个夏尔巴人的脸,发现是个年轻人,可能才刚二十出头,眼睫毛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冰。
“嘿,你怎么样?”明玛用尼泊尔语说。那人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明玛把手放到那人肩膀上摇了摇他,又说了几句“喂,醒醒,你还好吗?”之类的话。过了一会儿,那人动了动,慢慢抬起头来。他想说话,但说出来的话都杂乱无章。明玛看着乔伊舍尔,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他这情况不妙啊。”
明玛拉下那男子的面罩,放到自己脸上。什么都没有。随后他打开那人的背包,里面装满了氧气瓶。他是背夫,在为其中一支登山队运送氧气。他一定是落在了后面,自己的氧气也用光了。
明玛给他换上一个新氧气瓶,把流速开到最大。他说:“等几分钟再看看会怎么样。”
乔伊舍尔和明玛静静坐在雪地上,看着那个夏尔巴人,希望氧气能让他清醒过来。乔伊舍尔当然也明白,他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真正”素食主义者的梦想究竟能否实现,现在还不好说。在珠穆朗玛峰高处陷入麻烦的夏尔巴登山者不可能指望别人救援,因为唯一真正有机会施以援手的只有其他夏尔巴人,然而他们自己的客户通常都照顾不过来,他们又不能把那些客户扔了不管。但这时候乔伊舍尔认为,如果这个人无法恢复过来,他和明玛会放弃登顶,尽力营救他。他们没有商量过这事儿,但他毫不怀疑,明玛也是跟他一样的想法。乔伊舍尔认识到,是因为自己以前登过顶,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但如果他从前没登顶过珠峰呢?如果他是在2016年碰到的这个夏尔巴无名氏,他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