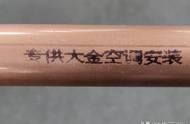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到了情不自禁回顾往事的时候,这个人或则步入了人生之秋,老了闲了,或则当境并不称心适意,因为他回溯的过去,往往与眼前映照作比,招致自己的情绪坠落走低为伤感忧怨……我觉得这话不错,但它只说对了部分。还有一种情景,那就是有些人七老八十,老大不小的年龄,却仍未回首总结回望自己的一路走来,那是因为他尚在打拼,尚在盯着眼下的生存人际,无暇顾及既往!
人的历史具有所有事物基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块组成。过去已经发生,否定还是承认,它都不可更改地留存在那里,映证着我们的曾经。但它可能因为岁月的远去,记忆的疏离,变得模糊而缺少清晰;现在是当下最真实的存在,无论是畅达快意,还是愁肠百结,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是身心皆在的融合,需要如同哈姆莱特是生还是死的研判,需要所有的勇气直面,需要步步审慎使它成为历史后不留污点;未来可以预期、设想,却尚未发生。所以我们得严阵以待,力争让变为现在的未来不留瑕疵,心安无悔地越过自己的生命时光。
当然受命的回忆文章自当别论,犹如本篇:
我是1981年秋考入榆林学院的,当时学校准确的名字叫:陕西师范大学榆林专修科。但我们不这么叫。无论书信来往还是日常言及,我们都会称“榆林西沙师院”,偶尔在正式的场合称“榆林师专”。严格意义上讲,我来报到的地方是更名“榆林师专”后绥德师院的新校区,也就是今天榆林学院的雏形。今天榆林学院的实景,绝大部分当时在规划图里。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秋天。从榆林老城越榆溪河只有现在人民中路一座桥,且河西多为沙地,路面既无柏油也无水泥,沿途只有零散民宿(卜壳窑)和几个单位:如那时的185地质勘探局只是些安置在沙丘上类似于火车车厢式的简易房;另外就是榆林三中、榆林治沙研究所和南郊农场的养猪场,再往西数公里的地方是市农校。更多纳入眼帘的是戈壁、沙丘,或“长河落日圆”的塞上风光。报到了方知学校暂时只有中文一个专业,其余的数学、化学、物理系尚在绥德丁家沟老校区。在往后的数年里,它们陆续迁入现址。整个西沙,可以说路旷人稀,只有一家说是百货其实也就日常用品的门市,矗立在三中对面路边的沙地上。稍有点紧俏的货物和新鲜的菜蔬得跑进城采购,或借自行车或步行成为乡下人进城的开心。当时的自行车还不是人人皆有的稀缺物,所以不到周末,我们便早早地问候有车人是否用车?然后就预订了。那时的阳光灿烂无比,也许是因绿植较少的缘故,照耀得泥土滚烫,但我们时时浸淫于青春的欢畅。还有那无数次看不够的大漠晨曦、塞北夕阳——
那时的校园只是个概念。除了一栋已投入使用的教学楼,和一栋在建的科研楼,其余就是校园的东南角和操场尽头的十几栋两层的卜壳办公和学生宿舍区域。也就东南角圈有围墙;围墙的东边留有大门。除了办公、宿舍区域和操场的地面积土硬化,或建有甬道和花坛外,教学楼和科研楼的四周尚为沙地。当年的春冬季,总是大风扬沙,黄尘蔽天时节。沙尘比柔顺的雪幕还武断地截断了视线,挟裹着颗粒,击打着脸面。防风帽、纱巾和口罩是必备之物,比护肤霜要受用得多。入校后的每个春天,学校会组织师生到学校的四址去植树,作为拥有地界的宣示。印象里当时的学校地貌,是东西望不到头的狭长状,东与185毗连,西抵林校水渠前,北达聚财巷,南极治沙研究所。与后来所见一些隐身于大都市名校的狭小相较,辽阔了个去!
从1981年秋入校至1985年7月中调离,我在榆林学院整整地生活了四个年头。这四年里我以两种身份出现:前两年也即1981年秋至1983年秋,我是就读于学校中文专业埋头学习的学生;1983年秋至1985年秋,因留校图书馆我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留校期间,期待着出外深造后某天走上讲台,执鞭施教。早年曾有过当画家、作家的情结,但在毕业就业的眼前,教师职业却成了我的首选。
我在母校的四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长头发、喇叭裤和收录机盛行时节。条件艰苦是艰苦了些,但思想空前活跃,新旧观念碰撞骤烈。虽说校区只有一栋教学楼在用,一栋实验楼在建;另有十一二栋两层卜壳办公和住宿小楼,但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那十几栋卜壳楼侧至今有我当年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书写的斋号;那时没有校报校刊,只有一份《三好简报》,蜡纸刻版的四开四版小报,每月一期;1982年后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我任主编一年;这四年里,我曾参加北斗诗社、集邮协会,更多的时间习练书法,业余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当然少不了那些令我敬畏的师长和同学们的友谊,特别是与学兄王立轩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地一块度过了愉快的4年。更主要的是在这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成为自己成长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榆林学院的4年,给了我人生精神追求里最基本的东西,让我感念终生铭刻永记。
人生苦短,转眼间激荡的40年岁月流逝:40年间,我们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参与和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也看到了榆林学院——自己的母校——在人才培养输送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