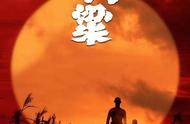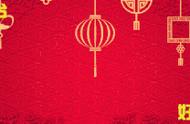也有人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后,认为它是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这部作品与《百年孤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这两部作品都确立了悲剧的主题,揭露了人性的扭曲;这两部作品都具有“魔化的现实主义特征”。
对此,莫言也作出过说明:
“《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而《百年孤独》的汉译本是1985年春天才看到的。”
在莫言看来,《红高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
有别于传统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直接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爸”,将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得表达出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也是这部小说当时广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王小波说:“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戴凤莲是一个充满野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女人。她有着鲜明的个性,敢作敢为、不喜欢被“封建礼教”束缚。
用原文的话说:“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提起旧社会的乡村农妇,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或是想起像祥林嫂那种逆来顺受的女人。
毕竟,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在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女性的天性难以得到解放。
但是,解放天性,从来都不专属于孩子和艺术家。对任何人来说,天性越是被压抑,人就越渴求解放。
莫言说,“《红高粱》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它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戴凤莲不想因为一个男人的条件、和适婚年龄,就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就像她不想绑“三寸金莲”,却又不得已而为之一样。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戴凤莲没办法改变父母的想法,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再次遇到余占鳌后,戴凤莲不顾已婚的身份,在充满自由、充满野性的高粱地,戴凤莲终于与余占鳌抱在了一起。
与余占鳌这个土匪男人相处时,戴凤莲颠覆了女性一贯的柔弱形象,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惧男权,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为了挽留人才,会毫不客气地质问余占鳌,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
然后向余占鳌不惧不怕地喊道:
“开枪吧!”

知道余占鳌和兄弟们去打日本兵,戴凤莲不顾危险,做好午饭后,亲自去前线送给他们。这才遇到了日本兵的枪林弹雨,倒在了高粱地里。
纵观戴凤莲的一生,既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又有对天性解放的崇尚。
而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时间,正是吸收西方文化,人性意识觉醒、渴望自由、摆脱压制的年代,《红高粱》乘势而上,为长期自由和天性受到压抑的中国人说出了“心里话”。
正如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那样: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该做的都做了,该*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追求自由,解放天性,对每个人都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