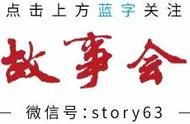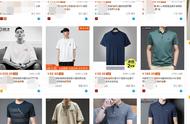《爱斗蟋蟀》刊于《点石斋画报》(1884—1898)戊集第八期
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加快,新兴娱乐的层出不穷,斗蟋蟀这项古老的民俗娱乐虽然不及历史时期的“全民娱乐”,但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型城市中都设有蟋蟀协会与俱乐部,每到秋季都会有无数的斗蟋蟀比赛与研讨会。对于斗蟋蟀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玩物丧志的罪魁祸首,蟋蟀宰相贾似道、蟋蟀皇帝朱瞻基无疑是世人嘲讽的对象;有人认为它是怡情养性的妙物,宋代诗人黄庭坚曾赞美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而不降忠也,败而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斗蟋蟀作为一项古老的民俗娱乐,我们不宜以玩物丧志来一刀切地否定,更不宜对其过度沉迷,让其游戏人生。娱乐须有度,斗蟋蟀对于人们扩大社会交往、丰富动物学科普知识以及树立公正的处事态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山东的宁津县与宁阳县的村民每逢秋季都会斗蟋蟀,他们非但没有不务正业,而将蟋蟀成为当地的朝阳产业。每到秋季,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夜间到田地里捕捉蟋蟀,白天拿到街上贩卖。据统计,秋季蟋蟀的交易额占当地村民收入的70%,蟋蟀产业是当地村民致富重要途径。当地甚至流行一句俗语:“一只蟋蟀一头牛”,足见小小蟋蟀里承载的巨大经济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与空闲时间的增多,在适度的范围内斗蟋蟀不失为为一种传统而又时尚的娱乐。



宁阳集市上蟋蟀交易 与北京自由市场的蟋蟀
参考文献:
[1](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金笼蟋蟀》,明顾氏文房小说本。
[2](清)华希闵:《广事类赋》卷40《蟋蟀》,清乾隆二十九年华希闵刻本。
[3]孟昭连:《中国古代的蟋蟀文化》,《寻根》,1995年第1期。
[4](宋)贾似道:《促织经》卷上《促织论》,明夷门广牍本。
[5](清)陈淏子:《花镜》卷6《附录养鳞介法·蟋蟀》,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
[6](清)朱从延:《蚟孙鉴》后卷《杂备法·捉促织法》,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7](清)朱从延:《蚟孙鉴》后卷《杂备法·捉促织法》,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8](清)朱从延:《蚟孙鉴》后卷《杂备法·捉促织法》,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9](清)朱从延:《蚟孙鉴》后卷《杂备法·捕捉歌》,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10](清)朱从延:《蚟孙鉴》续卷《蓄养之异》,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11](清)朱从延:《蚟孙鉴》续卷《斗彩时局》,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12](清)朱从延:《蚟孙鉴》后卷《较胜法》,清乾隆刻四十一年补修本。
❤❤❤❤❤❤❤❤❤❤❤❤❤❤❤❤❤❤❤❤❤❤❤❤❤❤❤❤❤❤❤❤❤❤❤❤❤❤❤❤❤❤❤❤❤❤
作者简介:佘燕文,女,1994年2月生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宠物文化史。
【游艺民俗】责编/晏秋洁
图文编辑/晏秋洁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北师大民俗学*bnufolk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