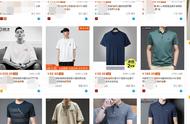小的时候住在科学院宿舍,那是个平房院,一到夏天满院子蛐蛐儿叫,院里男孩子十几号,能忍得住不去抓一两个来比画的几乎没有。后铁门处的蛐蛐儿尤其善战,周围几个院儿都有来抓的。
蛐蛐儿有很多品种,其实差别细微,比如青头和棺材盖儿,院儿里当爹的一水儿研究员,就没一个能分得清,但“油葫芦”是肯定能区别出来的。
“油葫芦”,是我们对雌蛐蛐儿的称谓,因为雄蛐蛐儿尾须两支,雌蛐蛐儿三尾,多一个产卵器,形如长嘴油壶而得名。也有兄弟说我对“油葫芦”的定义不对,“油葫芦”与蟋蟀不是一种昆虫,雌蛐蛐儿不叫“油葫芦”,但确实有被鼓捣出能斗的来,叫“三引大扎枪”,不知真假,且存疑。无论如何,让雌蛐蛐儿开牙打斗,无论人还是蛐蛐儿,纯属一种变态。
斗蛐蛐儿都是斗公的,就跟现在街上老爷们儿经常打架、大姑娘经常看热闹鼓劲一个意思。再没听说过“油葫芦”也能斗。
可是,总有些人比较笨不是,抓不到公的,就琢磨用母蛐蛐儿上阵。
这应该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嘿,就有我们一哥们儿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哥哥是矿冶学院的,不知道用了什么原理调和出一种绿色药水,往“油葫芦”脑盖上一抹,那蛐蛐儿立马一反常态,纵蹦蹿跳,逮谁掐谁,跟亚马逊女战士似的,张牙舞爪地倍儿欢,一时传为奇谈。问题是这药十分奇怪,多好的蛐蛐儿,让他的“油葫芦”咬了都从此不再张嘴,成了“臭嘴捞眯子”,后来闹得谁也不敢跟他斗,这哥们儿郁闷得就差自己下场子了。
也未必是药的作用,想想,蛐蛐儿也有面子啊,大老爷们儿让一姑娘追着打,咬得满身是血,搁谁还有面子到处跟人叫板啊!
当时我们的宿舍离动物所和遗传所都不远,那里是童第周教授让金鱼和四脚蛇结合生孩子的古怪地方,那属于国家重点课题,有解放军站岗,按说大家该敬而远之。可那里面有金鱼池(做试验用的,露天),可以偷到金鱼——偶尔可以偷到长相很古怪的金鱼,搁今天该有人往核辐射上联想。那金鱼池附近草也很多,蛐蛐儿成群结队,我们这帮孩子经常跳进去偷偷捉蛐蛐儿。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有再被解放军抓了的。
好在人家也知道克格勃或者CIA都不会雇这种墙都翻不利落的童工,恫吓有之,最后无一例外轻松放人。

不过也有发生奇遇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兄弟被抓了,有个搞研究的老爷子看见,走来问问,还饶有兴味地检查他抓的蛐蛐儿,等看到里面多是三尾的母蛐蛐儿,不禁摇头,说:“外行啊外行,这三尾的蛐蛐儿不能斗。”
我们那兄弟大着胆子说:“能斗。”
老先生说:“你怎么胡说啊,公蛐蛐儿为争母蛐蛐儿斗,母蛐蛐儿为什么斗?跟你小孩说这个你也不懂……”
“就是能斗嘛,要是能斗你放我走?”我们那兄弟一看有门,科学院的孩子都不笨,赶紧见缝就钻。
老先生说:“行啊,搞遗传搞了30年,见过金鱼长腿,我还没见过母蛐蛐儿开牙呢。”
我们那兄弟就地一坐,抓个旧罐头盒来,放进一公一母俩蛐蛐儿,顺手掏出一个小眼药水瓶来,照着“油葫芦”脑袋上就是一滴。
不等用蛐蛐草促战,只见那“油葫芦”脑袋往上一仰,翅子一立,跟打了鸡血一样,冲着那公蛐蛐儿就猛扑过去了。公蛐蛐儿看到来了一个蛐蛐儿MM,大概正满心琢磨怎么上去泡,忽然看见这MM扑过来又撕又咬,凶悍无比。那年头无论人的世界还是虫的世界都不流行野蛮女友,这公蛐蛐儿一愣之下,一边的翅膀已经给拽得跟散架的雨伞似的了。打到这个地步,惊骇莫名的公蛐蛐儿哪有心恋战,掉头就跑,一个追一个逃,看得老头儿两眼发直之际,那公蛐蛐儿一个超水平的狗急跳墙,蹿出了罐头盒夺路而逃!
老先生摇头晃脑,那叫一个不可思议啊,不过,然诺就是然诺,只能放人吧。
“人可以放,那小瓶绿色药水要留下,”老先生说,“我得研究研究这是什么成分。”
多年以后,在报纸上看到有报道搞运动的吃兴奋剂,正好当时我那兄弟在场,一扶眼镜,蛮紧张地问我:“老大,这不会是遗传所那帮人*吧……”
嗯……
摘自《故事会》文摘版201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