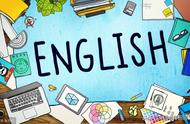(向左滑动欣赏全卷)
图2 林景辉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作品
草草书自作诗《登黄山二首》卷
万壑松涛百丈梯,巉岩绝壁挂虹霓。
漫摇疏影金光碎,清响密林黄雀啼。
道陡腿沉身渐老,观奇眼豁意犹迷。
微才欲运风云淡,未觉情深日已西。
深秋高日客迎蕃,色染重林众彩暄。
壁上危松鹰乍举,崖间怪石兽将奔。
莲台坐对千峰寂,寰宇搜罗五岳尊。
我欲因之长炼宿,无边妙境共轩辕。
周德聪(中国书协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林景辉的两件草书自作诗(一横卷、一中堂)及一件行草李白《游泰山六首·其一》条幅获得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按本届“兰亭奖”征稿启事要求,3件作品中一件须为自撰,林景辉提交了两件自撰诗文作品,其中一件用草书抄录他的自作诗《登黄山七律二首》,另一件则是七律《源流·时代——绍兴论坛感赋》。前者是登黄山则情满于山的抒怀,后者是临曲水则意溢于书的感赋。于此可知林景辉在传统文化古诗词上的修为。在书家沦为“文抄公”的当下,他的自作诗及创作的确具有“引领性”意义。
抄录古诗文尤其是经典的耳熟能详的古代大家的诗词,在“书法热”持续的几十年里,可以说很多人都这样干过,且不乏优秀创作,个中所形成的范式多被后人模仿,无论是借鉴也好,还是不自觉地“拿来”也罢,都可能在特定的时空有模有样地混迹于各大展览甚至获奖。但是自撰诗文的书法创作,无所依傍,因此创作起来自有其难度,它必须仰仗自己平素积累的书法艺术语言,在一次性挥写中将功夫与性情完美呈现,才有可能得到评委与观赏者的认同。林景辉的《登黄山二首》草书横卷与草书中堂《源流·时代——绍兴论坛感赋》很好地展现了苍茫劲健、豪放郁勃的线条之美,也印证他在“习草将迷”的过程中对传统经典的有效法乳。在他的草书中,既有张旭用笔电击星流、翻飞腾挪,怀素的圆转通透、挥运自如;亦见山谷的潇洒流落、遒逸劲健;更有觉斯的厚重沉雄与连绵铿锵,重按轻提,顿切绞转,疾涩互渗,方圆并运,将激情贯注于笔端,使之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正所谓“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更兼其结字大小悬殊,纵敛殊异,奇正相谐,与行气的疏密掩映、摇曳多姿,形成了章法的既茂且疏,于笔墨的轻重交替里组构成五音繁汇的乐章。草书中堂因其纵向取势,笔墨有如暴风骤雨,用笔的裹、绞、*、皴,纵情恣肆,老笔纷披。奇音在爨,万象在旁,此之谓乎?!
清人刘熙载尝云“观人于书,莫如行草”。非他书不能尽功夫,实行草可以达情性。这不仅与人的审美境界有关,更与人的深情至性相连。林景辉也曾如许多习书者一样,因为爱好书法,“篆、隶、楷、行、草无所不涉”。后痴迷草书,“初法《十七帖》,继习《书谱》《小草〈千字文〉》……又师山谷、觉斯,参从碑法,并效时贤之笔墨”。从这一夫子自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草书学习的清晰路径——由小草到大草,由精致向豪放的转变。而且他不讳言向时贤取法。窃以为学习书法,厚古不薄今方为正途,惟要“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乃佳。如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非草书不能擅其胜。故林景辉在骎骎学书的路上,找到了草书,并寄情于此,试图“书以身化”,神与物游。
他的行草李白《游泰山六首·其一》条幅相较于草书横卷与草书中堂,虽有潇洒之态,却相对紧敛许多,盖他所使用艺术语言有些许的不同——许多字采用了行书化的写法,间用草书使之畅达,严格意义上看,它是行书与草书的集合。在这一件作品中,王铎书风对他的影响尤深,也适量汲收了颜鲁公与米襄阳的笔法体势,厚重沉雄,劲挺爽健,也是一件不俗的佳构。
书法之难,并不在对经典的临仿如何像,以至于达到乱真的程度;也不在对字结构记忆准确,可以在创作中随意调遣,更不在形式上的逼似古人,几近“文物”的模样,而在于气韵及神采,还在于古人之“气”与今人之“气”的沟通与融会,更在于如何从古中蜕变而出,形成自己的语言,即风格的诞生。唯有如此,“风格即人”方可坐实。以此观林景辉书,尽管他已在古人与时贤之间,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从更高层次上要求,他的作品还未能达到“有我”的境界,哪怕他的草书在狂放的书写中似乎“忘我”了。古代经典的草书文本,都是真真切切的“这一个”,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徐渭诸家,单单抽出几字或一字就能辨识,而林景辉的草书,尽管我们可以抽出许多像某经典作品中的字(那也只能证明我们对传统经典的认可),但很难看到属于他自己的独创又暗合于古人的形象。也即是说,今之书家,多在“展览体”的裹挟之下,似乎渐渐失去了“自我”。这一点也是值得林景辉警省的。

林景辉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作品
草草书自作诗《登黄山二首》卷(局部)
杨吉平(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兼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林景辉的作品和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获得者崔寒柏的作品不在一个层次上,而且远远不止一个层次。这个差距绝不是金奖和银奖的差距,金、银奖的差别只是一个档次,而他们二人的实际差距至少应是三四个档次。差在哪里?审美辨别力。一个书法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字又怎么可能写好?
林景辉先生的行书大概出自米芾,同时兼有诸家形影。其草书主要取法旭、素、黄庭坚而落脚于王铎。网查林景辉前几年的作品,主要是行草作品,私意以为要比这几件获奖作品好。之前的作品,尤其是十一届国展前后的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明丽爽目。行书线条饱满,行笔有力。草书线条干净圆润,行笔果断肯定,结字圆转富有张力,章法也非常自然。其第七届“兰亭奖”的获奖作品(图1—图3)则写得面目大变,甚至是面目全非。
变化之一是笔法大变,由中锋为主变为侧锋为主(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满目的侧锋笔触)。其次是流畅的行笔改为有意的枯笔、涩笔。再次是大量的方笔代替了圆笔。
“草贵流而畅”。侧锋在纸面的阻力显然大于中锋,必然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也自然造成观赏者的视觉艰难感。侧锋线条也往往宽扁,缺乏圆润的立体感。苏轼所言之“神、气、骨、肉、血”在林景辉的笔下只剩下一张皮,几乎完全失去健康优雅的笔墨美感。观其草书《登黄山二首》,好像似暴雨洗劫后的农田,一片残枝败叶;又像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在寒风中艰难前行,这难道是草书版的“流民图”吗?
枯笔燥墨的适当运用可以丰富笔墨的表现力。古人写字,枯笔燥墨往往都是在书写过程中因墨分减少而自然形成的,多非有意为之。线条涩笔的形成也大致类似,主要因为书家年老体衰,不能完全控制毛笔,书写时手指颤抖造成的。这种抖动而形成的战笔往往给人以苍劲老辣的感觉,有人书倶老的审美效果。但林景辉过度使用这种枯笔燥墨,给人以装老的印象。老是装不出来的,其草书线条的软弱无力感是无法与不装老的古人相提并论的。纵观当下,演艺界有些明星装嫩,而书法界则有一些书星们在装老,人心不古,境界日下,岂不有些滑稽?这大概是一种时代通病吧。
草书的一大特质便是线条的圆转刚劲。连绵草书当以圆劲流畅为其正脉。黄庭坚以楷法入草,多运以方笔,鲜于枢叱之曰:“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论草书帖》)黄庭坚草书卓然成家,鲜于枢之评固有失偏颇,但草书中方笔过多毕竟会影响草书的酣畅飞动之美,而林景辉的“兰亭奖”获奖草书无疑有此不足。
林景辉“兰亭奖”获奖作品不及崔寒柏“兰亭奖”获奖作品之处有两点:一是基本功不扎实;二是取法更低,笔下明显有当下流行书法的痕迹。这正是缺乏书法美丑辨别能力的必然结果。怎么弥补这个不足?聪明如林景辉先生者应知道答案。
然而,林景辉的作品能获“兰亭奖”奖自有其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应该是他作品中的章法。在获奖作品中,其草书中堂的章法最佳。此作字法绵密,气脉相连,字形大小的自然对比也增强整幅作品的节奏变化,若单以章法而论,此作则几乎无懈可击。
值得注意的是,林景辉的两件草书作品均为其自作诗,其诗作格律严谨,格调不俗。然认真品读,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主要问题是语言问题。比如草书自作诗《源流·时代——绍兴论坛感赋》中堂最后一句“一篇痴心托素箴”中的“素箴”一词有生造之嫌,如果不是笔者孤陋,此处当为“素笺”而非“素箴”。但“素笺”在此诗中又不押韵(该诗用“侵韵”),故林景辉先生便造了一个“素箴”,为了就韵而生造词语。还有《登黄山二首》中也出现了“道陡腿沉”这样的口语,应是典型的诗病之一。自作诗值得提倡,但如果作不好,倒不如老老实实抄古诗的好。

图3 林景辉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作品
行草李白《游泰山六首·其一》条幅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于今满青苔。飞流洒绝巘,水急松声哀。北眺崿嶂奇,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庆旭(苏州市书协副秘书长):
很少有人的作品能像林景辉一样,真实地反映创作者真正的本源,能反映创作者这个活生生的人。
当代书法发展40年来,涌现出一批写王铎的高手,大致两个地方有代表性——王觉斯故地河南,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福建。作为远离中原腹地,亦有自身深厚文化传承的东南沿海经济富裕省份福建,书史上的名家可谓辈出,像北宋的蔡襄、蔡京,清代伊秉绶、林则徐等,仅明代就有可与王觉斯比肩的大轴类高手,像黄道周、张瑞图,都是福建人,为何当下福建行草书家撇下家乡人而钟情于数千里之外的王铎?颇使人奇怪。倘若有缘由,或者是特定时期领军人物的影响?福建李木教的王铎类行草书曾经风行一时。
林景辉的3幅作品让我打分的话,按百分制,行草条幅85分;手卷88分;草书中堂91分,另有天真率性加分(4分),总共95分。且让我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