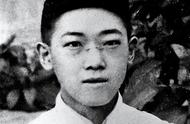图片来源于网络
——读书:《狱中杂记》
如慧:
夜里临睡前,点开罗翔老师的《圆圈正义: 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看了《代序》这一节。
在《代序》里,有这么一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如果人只是手段, 这会走向毫不掩饰的极权主义。如果人只是目的, 那也会走向过于放纵的个人主义。”
尽管躺在床上陷入沉思的后果就是直接睡着,可是在临前我却想起了前几天读过的一本文言文小说。这本小书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它就是《狱中杂记》。
这是作者方苞在康熙五十年受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的株连,被押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他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狱中杂记》讲的是方苞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通过从瘟疫起死者众多开始,慢慢讲到狱卒、行刑者、狱吏的狡诈与残忍,进而揭露官官相护,欺上瞞下,只手遮天,与犯人勾结牟利的黑暗现实。
以行刑者为例,此人在行极刑前,对犯人家属说:“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
什么是极刑?极刑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凌迟。
行刑者在行绞缢前,对犯人家属说:“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
稍有钱财而不想亲人受罪的,只能顺从而送钱财免其痛苦;无钱者,只能无力地由着犯人亲属临死前受尽痛苦而死。
方苞曾就这个事情问过狱中小吏:“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意思就是:“行刑者与犯人之间并无仇恨,他只不过是想要弄点钱财罢了。不过,如果犯人没有钱,能不能让他死得痛快一点,这也算是有点仁慈之心啊。”
小吏则说:“是立法以警其馀,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小吏则狡辩说:“这是立下规则用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同时用以警告那些普通人,不要轻易去犯罪。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会有人心生侥幸,随意违法犯罪。”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人会以为这是当年监狱中最痛苦最黑暗的事情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简单。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在刑部,有些老吏,私刻伪章藏于家中,常常用来偷偷修改各种文书。他并不完全改动,只是做些增加或者删减关键部分的用词或者话事,而执行的人却往往无法分辨出真伪,然后他就能从中谋利。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无法被查觉呢?当然不是,事情做多了肯定会被人发现的。但是,老吏并不怕,你看他是如何说的:“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
意思是:就算被查觉,我们固然活不成,然而主审官却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丢官弃职,甚至会被处死。他选择不会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我们也就不会死了。
果然,“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即:主审官被老吏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最终却不敢多说什么。
如果说法律是太阳,那么犯罪就是太阳上阴暗的地方。太阳无法消灭阴暗,法律也不能完全消除犯罪。
只不过,作为一个人,我们在追求公平和自由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外,在看书的时候,尽量地把现在看到的书与往日看过的书进行一个搜索联想,这样,就能不断地修正自己思维上的偏差。
我们是永远不能做到完美的,但一定要走在完美的路上,尽量让自己的内心安宁。
2021.11.23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