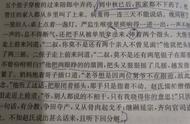早在我没读过《儒林外史》这本书之前,就“认识”了严监生——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守财奴形象。当然,我是从他那个“两茎灯草”的吝啬故事中知道他的,这个故事被各种文章引用,流传甚广。
故事是这样的:
严监生病重,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可却始终不肯断气。他说不出话来,只是顽强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有人问他,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没见到?他摇摇头;第二个人问,难道还有两笔银子没有交代吩咐?他把“两眼睁的滴流圆,把头又狠摇了几摇”,又使劲伸着手指;第三个人问,想来你是想着孩子的两个舅舅,要当面交代?连续听了三个人的话,严监生很失望,他闭上眼睛摇头,手指依旧指着不动。这时候,他的妻子赵氏过来说,别人说的都不相干,我知道你的心愿。“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说着她走过去挑掉了一茎灯草,严监生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断了气。
这“两茎灯草”从此成为经典故事,而严监生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吝啬鬼和守财奴,足以比肩其他各国的吝啬鬼形象。
后来读到《儒林外史》,发现严监生的形象很复杂。他不仅可怜可笑,其实也可悲可悯,可叹可感。

严监生名叫严大育,字致和。他是个土豪,家有十万银子,还有个“监生”的身份,算是有地位有体面的乡绅。但他还有哥哥严贡生,严贡生无论在家族中还是社会上,地位都比他高,让他时时处处都受气。严贡生生活奢靡,让弟弟严监生很不以为然,他在衣食住行上十分节俭吝啬,所以比哥哥富有多了。
除了临终怕费灯油之外,他还有以下一些节俭的事迹:
他平素不舍得买猪肉,有时儿子馋了实在要吃,便去买一小块哄哄孩子;自己生病了,却舍不得钱吃人参滋补,让病情一天天加重;时常他还带病算账,日日想着田里的早稻,焦虑不已……
不过严监生虽然很吝啬,然而相比其他各国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形象,却还大有不同。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有个守财奴叫葛朗台,他对金钱有着迷之热爱,经常半夜三更关在房中欣赏自己的金币。他把钱财视为至宝,妻子生病舍不得请医生,对侄子、女儿更是一分钱不给,是完全彻底的吝啬成瘾;俄国作家果戈里在小说《死魂灵》中塑造了一个泼留希金,这位更极端,他守着万贯家财,不仅丝毫不给儿女,连自己也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葛朗台和泼留希金都只爱金钱,毫无人性亲情,他们是彻底而纯粹的守财奴。

严监生不一样,他虽然自己不舍得吃用,对亲人还是十分慷慨大方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重,他“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还经常用人参、附子等名贵药材,一点都不心疼。王氏病重难治,同意将生了儿子的妾赵氏扶正,为了能让赵氏顺利正名,他送给王氏的弟弟王仁、王德两个舅爷各150两银子,出手也是毫无犹豫。临终之时虽然他惦记着那“两茎灯草”费油,却还是送给王氏兄弟“几封银子”做科举考试的盘缠,并将自己的儿子“托孤”给他们。不仅如此,他的哥哥严贡生仗势欺人被人告发到官府,自己害怕跑路了,官府来问严监生,最终他出钱请人给摆平了事。严监生出钱出力为哥哥埋单,固然主要是因为胆小怕事,但花这些钱时他并没有过多犹豫,事后也从无一句抱怨。
他与那些只爱金钱的守财奴截然有别,他是典型的中国式守财奴。
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父辈祖辈的影子。他们和严监生一样,见识不多,本领有限,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他们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不敢做丝毫违法的事儿,当然也不敢去“创业”。他们只能靠着辛苦和节俭一点一滴艰难地积攒着钱财,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钱财来得如此不易,他们当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买药看病。然而,他们并不是金钱的奴隶,他们有着丰富的人情味儿,对自己的亲人都很慷慨大方,需要时拿钱拿物,并无一丝吝啬。

严监生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省下一茎灯草对自己毫无意义,他不肯闭眼地手指灯草,除了节俭的习惯之外,一定是想着多给自己的妻子儿子留点东西。在他的心中,多留一点是一点啊!这是过分的节俭,这也是深情的牵挂,此情此景,真是让人心酸又感动。
这是中国式的守财奴,不是对金钱怀有天生的执念和变态的热爱,只因对贫困的惊恐,对自己辛苦劳作的珍惜,所以才有这样的表现,虽然可怜可笑,却有是可悲可悯,可叹可感。
不舍“两茎灯草”的不仅是严监生,也是我们的亲人街坊。他们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他们不惜金钱、掏空积蓄为儿女求学买房,而自己却节衣缩食,时常在寒冷难捱、酷暑难耐时,也舍不得打开一天空调,为的是省下一点电费……
这是中国式守财奴啊,我们其实没资格嘲笑严监生。也许,我们也正走在这条路上……
北方丽人:一个喜欢历史、爱读书却不够优雅精致的女子;一个爱孩子爱教育却不怎么成功的教师。红尘中因文字与你相遇,就是我最大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