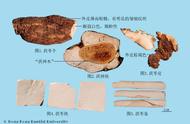新娘子的到来让杨家坳热闹极了,轿子落下,一群调皮的孩子挤在轿门前,吵吵嚷嚷,探着脑袋寻新娘子身影,远近乡亲都赶来凑热闹,一时间笑声、哄闹声、锣鼓声无节奏地交织在一起,竟和谐般地奏起“喜宴”的乐歌。
萧萧的婆家是这个偏远村落的大户人家,家中几十亩田地,还雇了两个长工哑巴和花狗,一起帮衬做工,日子算是富足又生气。婆家有一个独苗儿子春官,3岁的娃娃走路还不稳当,终日缠着母亲要奶喝。
大喜的日子,新郎官不知怎地,哭闹不停,心急火燎的母亲,把孩子抱入怀中,给他唆了两口奶,便作安抚。

正厅大堂上,萧萧跪在地上等着丈夫一同行礼,春官被婆婆抱过来,小家伙竟非常不给面子,一撂挑子,往地上一躺,打着滚哭啼,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萧萧撸起垂在眼前的珠串儿,偷偷望了一眼春官,也被逗乐了。
不得已之下,家人只能安排一只大公鸡代替春官,与萧萧完成了拜堂之礼。
在这里,萧萧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湘西女儿,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成为童养媳,早早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命运自出生时就已经被剥夺。一场啼笑皆非的成亲礼,无情阉割了天真少女的一生,看得人心里五味杂陈。
关于“女学生”的谬谈,实是传统礼教与认知觉醒的对抗过了门之后,萧萧应着规矩,叫小丈夫作“弟弟”。婆婆算是脱了手,将儿子全权交给萧萧。能*萧萧一面绩麻、纺车、洗衣、种地,一面细心照顾着小丈夫。

萧萧用一口背篓驮着小丈夫,钻在田间地头玩耍,或是爬上草堆子,带小丈夫看月亮,轻轻唱着歌谣哄他入睡。
不论做什么,到哪里去,小丈夫总跟在萧萧身后,小丈夫有些方面很怕她,当她如母亲,亲昵得很。
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萧萧长大了。在婆家虽有干不完的家务活,身体劳累,但白米饭管够,萧萧一下子蹿成了女人样子,但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

这日,晚间饭罢,一家人坐在院子里闲聊,两个长工簇在祖爹身旁,花狗把在城里看到“女学生”的事情说给众人听。
花狗的描述里,女学生没有辫子,像个尼姑,穿着短袖上杉和半截白裙,细嫩的胳膊和大腿,赤裸裸露在外面,让人没眼看。
众人听后大笑,仿佛花狗口中的不是人类,而是天外来客,近乎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的人,与他们这个遥远的村庄没有半点关系,可以当做怪谈笑上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