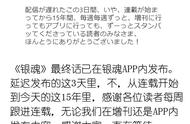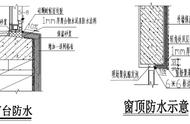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在文风卑陋的大背景下,对为文自然的肯定与提倡。文学理论中的“自然”,起源甚早,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中已经有关于“自然”的命题存在。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文心雕龙》
“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 《文心雕龙》
刘勰笔下的“自然”,既包含了人性所散发出来的真实情感,也包括了进行文学创作时自然流露、不事雕琢的言辞表达。萧纲在评价谢灵运的诗歌时称
“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
对谢诗的“天然”表示赞赏的同时,又对其未能全然表现出真性情而进行批判。由此可见,其时,“自然”就已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学审美形态。至唐代,文学家亦如南北朝批评家一样, 极力主张为文应出于自然之性情,创作过程也须“自然”。
然至韩愈引领的古文运动确立了构建“文统”的意识之后,“自然”与道统便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也被赋予了“道”的高度和内涵。

西蜀是道教的发源地,道家思想给当地的文人学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到了宋朝,巴蜀地区依然是道教的大本营,巴蜀本土文士,有很多都是“阳儒阴道”。田锡生于洪雅,道家思想自然对田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文学上。
田锡关于“自然”的论述,即是基于唐人的理论,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生发的。他在与友人宋白论文时称: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 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 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
田锡认为,“性”与“情”都是本乎自然的,为文须以自然为尚,性情相合,而不应受常态、定文的桎梏,随性而发,写出来的诗文才会有“声气”。他所指的“为文自然”,不仅是合于人之性情,同时还要顺乎自然规律。
作为一个文学家,田锡有着自己的创作体验,他描述自己文学创作时的切身体会,亦是随心所至,自然而为之:
“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稀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濛,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
很显然,田锡的思想秉承了南北朝以来的“自然”,且与唐人所谓的“自然”不同,他更加关注的是创作过程中的自然随性和语言的平易流畅。

田锡“文法自然”的思想,正是针对五代时期文风的刻意造作而提出的,在当时文坛可谓开一代风气。 同时,田锡自出机杼,主张“诗变于文”。他在《贻陈季和书》中写道:
“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 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迩来文士,颂美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神鬼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
将诗和文的功能区分得很清楚。“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之传统,田锡同样认为诗歌是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因此对诗歌这种“变体”采取的是不同的审美态度和评价标准。为了矫正宋初遗留下来的五代时期过于艳丽华藻的文风,在诗文创作上,他提倡平易清新之风,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他对元白诗歌风格的欣赏。
在赞扬友人诗歌的时候,他往往以元白作比,如称宋白的诗歌“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 吟”,赞陈处士“狂才意度若元白,满笺灵怪如麟凤”,足见他对元白诗风的倾慕。同时,在诗歌创作上,他也有意效仿元白之体,学术界一般将其归入“白体诗人”一类。然而,这并不表示田锡对诗文的审美趣味仅限于一种体式,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五代文风的全盘否定。 首先,对于那些富于才气,出人意表的神来之作,田锡是持支持和赞赏态度的: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 之?”
其次,对于文采斐然、想像丰富的诗歌,他指出其亦有值得称道之处:
“然李贺作歌,二公(韩愈、柳宗 元)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认为李贺之诗新奇诡谲,却受到韩、柳等儒士的赞赏,更加证明了“变态”之诗存在的合理性。对五代时期盛行的宫体诗,他亦采取包容的心态:
“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
田锡的诗赋中亦有此类作品,如《晓莺》:
“春宵已阑更点急,烟柳蒙蒙露花湿。画堂深邃楼阁寒,碧纱窗中月华入。早莺百啭催朝阳,簧言绮语何铿锵。云飞雨散梦初破,闻时满枕梨花香。”
其语言细腻华美,颇有五代绮丽诗风之余韵。由此可见,田锡反对的是五代过于淫艳且于时无补之作,而并非对其全盘否决。然宋初很多文士,对五代文风都是一概持反对态度的。如与田锡同时的柳开,就极其反感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辞华于理”的文章,
“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理华于辞,则有可视” ,
柳开推崇的是“理华于辞”的文章,甚至认为那些过于华美的文章毫无可观之处。其完全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多样性。
田锡之所以有这样不拘一格的见解,和他所生长的蜀地文化是分不开的。后蜀时期,蜀地偏安一隅,生活富庶,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稳定,蜀后主孟昶纵于声乐,喜好浮靡 艳丽的文风,士人争而为之。
广政三年(940 年),尉卫少卿赵崇祚编《花间集》,收录了大量蜀中地区的文人词作品,多以辞采华美为主,对西蜀地区的文学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田锡生于后蜀,前半生都在西蜀度过,其文学审美情趣必然受到这种绮丽文风的熏染。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士,田锡提出了与柳开等人相对立的文学观,他不仅意识到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还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客观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避免了在革除五代诗文之弊的同时走上矫枉过正的道路,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
三、文统与政统五代乱世,儒门淡薄,文士的时事精神亦消失殆尽,其诗文多为应承酬唱或抒发自身情感而作,甚少体现出对时政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