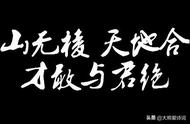疫情期间根据囤备而裁定餐桌之丰俭,很正常,但由此而高谈二餐的养生优越性,就未免矫情了。

朋友最近多次与我激辩,缘起二餐。他自诩“二餐”了,似乎加入了什么“勋业”似的,很高光的气象,这本无不可,疫情期间根据自己的囤备而裁定餐桌之丰俭,很正常,但由此而高谈二餐的养生优越性并称“古人都是二餐的”,言外之意还是“优秀传统”,就未免矫情了,好比宅家日久皮肤白了,头发长了,就大谈“苍白的高贵性”与“蓄发的飘逸美”,有意思吗。
然而辩论一向是推动考据的,首先这个“古人”的古,“古”到什么时候呢?考证了一下,“二餐”之最古,而且成“制度”的还是殷商时代,那也未免太古了吧。甲骨文中常有“大食”与“小食”之说,据考,分别指一天中的朝、夕两餐,相当于现在的早饭晚饭,那么根据书证,殷代基本是两餐,卜辞是记载王室贵族的活动的,贵族尚且“二餐”,平民不可能有更奢侈的三餐,然而,殷人二餐,并非因为营养学上的优越性,更非“断食修炼抗疫”,而实在是“米甏里米忒少”也,彼时生产力低下,农具不是木头就是石头、骨头,比如木犁石铲骨耜,绝大多数还是人力拉犁,那地里你能指望多少产出?
《周礼·膳夫》有“王日一举”的记载。举,就是*牲为肴,东汉郑玄解释,周王每日早饭都要开荤(*牲)的,但中饭与晚饭则不再另*新牲,而是吃早饭吃剩的肉食,这至少说明东周时的显贵都已一日三餐,爰至春秋战国,铁质农具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力更为飞跃,粮食多了,遂在全社会确立了“三餐制”。
成书稍晚的《战国策》“管燕得罪齐王”章有“士三食不得厌,而君鹅鹜有余食”一语,意思是你养的鹅鸭饲料吃不完,而你的食客却一日三餐吃不饱。
显然战国时的“食客”包括孟尝君门下的冯谖都是一日三餐制的,后者“食无鱼”还不干。查《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意思是如果郊游,往返只要备好三餐之粮就不会喊饿。也说明时人皆以三餐为习。

到了汉代,人们还给一日三餐赋予了专称,早饭叫“饔”,午饭称“shang”,晚饭谓“飧”(音“孙”),《说文》“shang”,昼食也。读音与“晌”相同,专指午饭。
可见先秦以下,汉唐宋元,一日三餐的习惯早已确立而且普遍,自然这是指正常的市井社会,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二餐”还是常见的,如若乱离之世或穷苦人家,则一日能一饭尚属幸事,更遑论“三餐”“二餐”呢?朋友之论,失在“都是二餐”,未免武断了。
至于“二餐”是否具有养生的优越性则完全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我之蜜糖,焉知不是彼之砒霜?
坊间盛传,朱元璋的手里,“二餐”差点成为制度,说他即位后似乎提倡过“过午不食”,那是他出身贫苦,而且深受佛门影响的缘故,恰如他所言,“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正好提倡廉政节俭的好风气。
问题是,贫苦人只吃二餐,是为无奈,出家人只吃二餐是为修行,你朝堂之上,倡廉可以,但“廉”到一天仅二餐,简直就枉为天朝了,须知所谓早朝,就是凌晨起床,清晨4时进宫列班,因为隔夜是空腹的,很多人非但肠胃受不了,而且极易“低血糖”,上朝“启奏陛下”时必然呈半死不活状,7~8时散朝后方能进食。午时的概念是11时至13时,则午饭12时开始到翌日4时的十多个小时又必须空腹了,真有类似的规矩,不要说大臣们会隔空“喊饿”,就是他的龙子龙孙如朱棣朱权诸王以及往后的宣宗英宗武宗之类的又有几个能遵守祖训不喊饿的,故而朱元璋真有类似的旨意我也以为是“圣主乱命”——而乱命照例是应该不从的。终明一世,还不是该三餐的仍然“日食三餐”吗,在圣旨与身体之间,当然是身体更诚实啦,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午摄入的能量能够让你撑过慵懒的下午,穿过漫漫长夜直到翌日早晨吗,况且旧时农民晚七点一过即睡了,而你的“夜生活”晚七点才开始,还说天天上网到子夜,你当你真能“禁足日久皮肤既白,须发复长,正好枵腹大谈苍白的高贵性与蓄发的飘逸美”吗?
言甫及此,门铃骤响,朋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居委米到!(胡展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