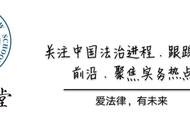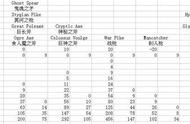1980年代萧乾和文洁若在萧乾的母校北京崇实中学合影。
“超人雪子”文洁若
本刊记者/宋春丹
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一栋塔楼的狭小两居室,是93岁的文洁若近30年的居所。丈夫萧乾去世后,她卖掉了挨着的那套两居室,在这里独居了20年。她说,自己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
窄仄的客厅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只有一部座机。最醒目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相框,其中最大的一张是萧乾在欧洲做《大公报》驻外记者时的黑白照,歪着头,笑得很灿烂,充满年轻的活力。
屋子里陈设破旧凌乱,但文洁若并不在意,因为书桌就是她的一方天地。一盏泛黄的老旧台灯旁摆着一本日历,记录着她每天的工作进度。她有太多事要做,要继续整理出版萧乾著作,还要翻译和写作。她说过很多次:“我这一生只做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来访的人很杂,她问都不问,直接开门。为避免来访者走错门打扰邻居,她干脆直接手写一张“文洁若家”贴在门上。但她希望来人有事说事,速战速决,不愿意多讲一句闲话。
文洁若曾告诉自己的忘年交“粉丝”、画家张斌,自己的姐姐们个个天资聪颖,她自觉不够聪慧,但是勤奋。她觉得,事实证明普通而勤奋最好,太聪明反易夭折。
文洁若生日时,张斌想去看望她,她不许,想等到95岁做一次大寿。她相信,自己可以活过享年111岁的周有光。
“可爱的家”
1953年暮春,文洁若第一次见到了萧乾,那时她26岁,萧乾43岁。
当时萧乾刚调来,社领导向大家介绍说,他暂时在家修改一部电影剧本,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送到他家里去。文洁若手上有部稿子,是从英文转译的苏联小说《百万富翁》,译文诘屈聱牙,校样改到第5次还不能付印,就提请萧乾加工。几天后,校样改回来了,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她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现在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文洁若被萧乾的学识吸引了,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自己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两人慢慢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深受外国文化和文学的浸染,都喜欢罗曼·罗兰、狄更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954年萧乾和文洁若的结婚照。
文洁若从未谈过恋爱,萧乾则有过三段婚史。萧乾向她坦言:“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忠告的声音一度占了上风,她曾与萧乾分手八个月,但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
1954年4月30日,他们利用午休时间去北京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萧乾雇了两辆三轮车,文洁若坐着一辆,另一辆载着她唯一的嫁妆—— 一只旧衣柜。萧乾骑着1946年从英国带回来的半旧自行车在前引路,去了他位于东总布胡同46号的作协宿舍。新婚之夜,文洁若还在灯下突击一部等着下厂的校样,不看完不上床,让第四次做新郎的萧乾目瞪口呆。
萧乾送给文洁若一枚精致的玛瑙胸针作为新婚礼物。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锦盒盖子的背面写着:“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署名:乐子。乐子是萧乾的小名,雪子是文洁若小时候在日本读书时的日文名。
进入文家的萧乾发现,文家总是弥漫着宗教音乐气氛。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萧乾也深受宗教的影响。他把由海外带回来的几百张西洋唱片搬出来,和文洁若一道挑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亨德尔的《弥赛亚》等,静静地聆听。
1954年深秋,秦顺新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上班。编辑室里只有一个扎着两只麻花辫的年轻姑娘在编稿子,她就是文洁若。秦顺新记得,文洁若正在编辑苏联百万字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废寝忘食,工间操的一刻钟也要抢时间睡觉休息。
1956年是文洁若最怀念的一年。继女儿荔子之后,儿子萧桐也出生了。萧乾发现自己每次抽完烟文洁若都会打开窗户通风,就自觉把烟戒了。休息时,他们会一起听古典音乐和相声。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三个孩子(大儿子为前妻所生)去公园游玩。
这一时期,是萧乾的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名字屡见报端,名声在外。他风华正茂,精神面貌极佳,经常愉快地哼唱美国民歌《可爱的家》。
“超人雪子”
这一年,在作协领导的动员和《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萧乾出任了《文艺报》副总编辑。他本不情愿,因为那是个“不祥”的单位,不少大作家都栽过跟头,而且他的本心是脱产搞创作,但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他只能答应下来,成为总编和三位副总编组成的班子中唯一的非党员。
很快,反右运动到来。萧乾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被打成右派。他被扣上“试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罪名,反苏、反共、反人民、亲美、亲英、亲日的帽子都戴在了他头上。
萧乾本是谨慎小心之人。1949年8月他离开香港回北平之前,给海外友人统统发了信,声明今后连贺年片也不能交换了。因为他对30年代中期的苏联以及战后的东欧了如指掌,知道像他这样的旅居国外者对海外关系应格外慎重。但这次,还是在劫难逃。

文洁若1950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照。
萧乾调任后,张光年提出把文洁若也调去,她觉得自己不是当记者的料,而且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也不放她。文洁若认为,没去《文艺报》是自己第一次拯救了整个家庭。《文艺报》作为运动的重灾区,自己去了一定会因与萧乾的关系被打成右派,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来人,光是古典部就有7个人被打成右派,5%的指标轮不到自己。
萧乾被打成右派后,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夜里,他常惊呼:天塌下来了!文洁若镇定地说:天塌了,地顶着。有人要她和萧乾划清界线,她拒绝了。萧乾说:“Maggie(文洁若在圣心学校读书时的英文昵称),这世界真冷啊,亏了还有个家。”
按照单位要求,她写了一篇揭发材料。她在材料中说,导致萧乾被打成右派的两篇文章与自己密切相关。因为自己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耳濡目染,萧乾才写出《“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因为自己和萧乾讲过人事科工作神秘,每个人的档案都放在一个绿盒子里,如果有人想陷害他人完全可以捏造假材料放进盒子里,萧乾受此影响才写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
这份揭发材料她先给萧乾看了,萧乾只字未改。材料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任叔时,王任叔没说话,只示意她放在桌上,文洁若觉得他可能根本没看。
1958年11月,文洁若调到亚非组,从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了日本文学的编辑工作。
文洁若日语基础扎实。7岁那年,她和姐弟们随赴日担任外交官的父亲到东京生活了两年。回到北京后,她就读于一家日本小学。父亲曾要求她把一套《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她每晚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4年,将10本书译完,总共100万字。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有了当翻译家的愿望。
文洁若当时的月工资是89.5元。萧乾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她每月还能从文联领到40元家属津贴。她要养三个孩子,还要赡养母亲以及没有工作的三姐文常韦。她曾花8天时间突击翻译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全文达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靠这一笔笔外快,她在萧乾被打成右派的22年间支撑起了这个家。她说自己是一只老母鸡,要把萧乾和孩子们保护在她的翅膀之下。
多年后,萧乾说,那时的雪子在他心目中是个超人。
从反右开始到改革开放前,文洁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与萧乾的通信阅后即毁,放在水里泡成纸浆扔掉。即便信中内容都是生活琐事,从不涉时局政治。
1961年,萧乾结束三年三个月的“监督劳动”回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
那时他们已从作协宿舍被赶到了前圆恩寺的一个大杂院,天天听着邻居的指桑骂槐,打定主意搬家。刚好文洁若得了两部译作的稿酬,就用这钱买了一个私房主贱卖的五间南屋和一间小西屋。三姐也搬来同住。他们戏称这里为“诺亚方舟”。
1962年,楼适夷又派给文洁若一项任务: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
钱稻孙和周作人的经历很相似。抗战爆发后,钱稻孙受国立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学校资产。北平沦陷后,他曾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当时日文译者虽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凤毛麟角,因此出版社领导常说:要趁周作人和钱稻孙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翻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出版。
楼适夷亲自带着文洁若去钱稻孙家,说给他带来个“女弟子”。出版社自1958年起,每月付给钱稻孙100元“预支稿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天商定,由于文洁若去学习,即月起调整为150元。
1962年至1965年,文洁若在钱稻孙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每周学习三个上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他译什么,她就学什么,实际上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她说,自己一生有不少老师,似乎没有哪一位称得上“恩师”,但钱稻孙确实是她的一位恩师。
1962年秋,文洁若曾请他和师母来家吃过一次火锅。不久,老先生专程乘有轨电车来出版社找她,说好不容易买到一只山鸡(那时食品相当紧缺),非请她和萧乾次日去吃午饭不可。
第二天他们准时赴约。萧乾早年读过钱稻孙用离*体从意大利语翻译的但丁《神曲》,十分钦佩,两人相谈甚欢。
萧乾对文洁若感慨:“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帮他抢救出一些译稿,该有多好!像他这样的大学者,今后上哪儿找去啊!”
“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停发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几位译者的预支稿费。1966年8月,78岁的钱稻孙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去世。1967年,周作人也在凌辱中去世。
1966年8月,萧乾也被关进“牛棚”。被逼无奈,三姐只得将萧乾多年来的手稿、卡片、札记、书信等付之一炬。
8月27日晚9点,文洁若下班还没走到家,就被一群人架着押往东四八条她母亲住的那个院子罚站。她母亲住的屋子黑咕隆咚,没有声音。那些人要她交待发报机藏在哪里,说她在美国的大姐是特务,她们母女也都是特务。审讯持续到深夜,有人喊把“老特务”也揪来一起斗。冲进屋才发现,老人已自缢身亡了。那些人打文洁若,一绺绺薅下她的头发,逼她在母亲的遗体前大声诅咒“死了活该”,直至天亮。她默默承受着,因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
萧乾也做出了与岳母一样的选择。他就着半瓶白酒吞下大量安眠药,幸被及时发现送医救回。面对从死亡边缘回来的萧乾,文洁若只是俯下身子,在他耳边轻轻用英文说了一句: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
文洁若问过萧乾,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萧乾可以选择留在剑桥,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也可以选择留在香港,继续从事新闻业。萧乾凄然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1969年,萧乾和文洁若及子女都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秦顺新与文洁若一家同属一个连队。他记得,很少有人接近这家人。
萧乾年届六十,却被当做壮劳力使用,说他是“大力士,能扛二百斤”。文洁若要他量力而行,被人汇报到连队,她挨了批,依然我行我素。排长让萧乾挖河泥,她就替他挖;让萧乾值夜班,她就白天干活,晚上替他值班。
1973年7月,文洁若被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萧乾也请假回京。他们原来的住房被占,新住处是一间土坯房,狭窄拥挤。文洁若在办公室将八把椅子拼在一起,睡了10年。
1979年,萧乾平反。1983年春节后,他们搬进了位于复外大街的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这是他们婚后第10次搬家。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他们还首次有了一间书房,叫“后乐斋”。
合译天书 《尤利西斯》
1990年,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约请英语翻译界大家译《尤利西斯》,约了一圈,均被谢绝。他又试图劝说钱锺书来译此书,并说叶君健说全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钱锺书回信说:“《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谓翻译来译的。假如我三四十岁,也许还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尝试;现在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了。”
李景端又找到了萧乾。此前的1989年,萧乾刚被国务院聘为新一任的中央文史馆馆长。80岁的萧乾想谢绝,但63岁的文洁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文洁若曾十年寒窗攻读英文。1940年,她小学毕业进入由法国天主教圣心会创办的圣心学校。她的四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学校读过书,她赶上了末班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从50年代起,她用业余时间译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且多为日文翻译。她始终记得,幼时在日本,父亲曾在书店指着一套日译本的《尤利西斯》对她说:“你看,日本人连那么难懂的书都翻出来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译,将来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
萧乾与这本“天书”的缘分更深。1939年他刚到剑桥时就购买了这套两卷本的书,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他以英国心理小说为课题,又重点钻研了这本书。1945年初,他还专程到瑞士苏黎世去寻访乔伊斯的墓,写下凭吊的话:“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虽然如此,但他对译这本巨著却犹豫再三。
文洁若先翻译了一章,给萧乾试阅,见底稿不错,润色起来不费事,萧乾才同意。1990年9月20日签订的约稿合同上,写的是“译者文洁若,校订者萧乾”。直到1992年,萧乾确信能保证译文质量又不至于把他拖垮时,才终于在合同上作为合译者而签了名。
萧乾在1991年7月写的《一对老人,两个车间》,记录了这段翻译生活。他说,他的同辈人多是儿孙满堂,像他和文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但他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也没有丝毫怨气,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
在这个“车间”里,他们流水线作业,文洁若当“小工”,担任草译和注释,做到“信”;萧乾当“大工”,加工润色,力求“达”和“雅”。两个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 work”。
他们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两个年龄加起来150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焕发了热情。两人都觉得,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过的也就是平生最美好稳定的日子了。
萧乾在书房兼会客室里写作,文洁若的书桌挤在卧室的大床边。书架几乎挨着天花板,她经常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她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连几个月不下楼。
萧乾说,在这项工作中,妻子是“火车头”。她的勤奋努力一直在改造着他,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他最佩服的就是妻子那摘“定额”的办法(文洁若说这是得益于父亲从小的训练),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文洁若最喜欢译瘸腿美少女格蒂·麦克道维尔的部分,这使她想起曾经患17年腿疾的三姐。三姐一直未婚,与文洁若和萧乾一同生活。
工作之余,文洁若唯一的活动是帮着三姐料理一些家务。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本来是萧乾的活儿,因为他又添了腰痛的毛病,文洁若把这活儿也接了过去。萧乾说,别看乌龟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文洁若把小乌龟隔离开,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
1994年,《尤利西斯》历时四年三个月,终于翻译出版。这是《尤利西斯》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成为文坛一大盛事。1995年,萧乾和文洁若在上海签名售书,创下了两天签售一千部的纪录。
独居岁月
1998年,画家张斌经人介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崇拜的这两位《尤利西斯》译者。
那时萧乾因心肌梗塞住在北京医院。文洁若在病房中安置了一张办公桌,一边照顾他,一边忙译作。
张斌觉得,萧乾与文洁若是互补性格,萧乾幽默、机智,文洁若实在、朴素,但她出席活动一定衣着得体,头发一梳,稍着淡妆,文化大家的内在风范就显现出来了。张斌送给了他们一幅画,是两朵鸡冠花,因为萧乾属鸡,文洁若算是嫁鸡随鸡。两人都很喜欢这幅画。
1999年2月,萧乾安然离世。进入半昏迷状态前,他不断地念叨着“回家,回家”。从他的遗物中,文洁若找到了一封留给她的短信,信中说:“谢谢你使我的灵魂自1954年就安顿下来。”
子女想接文洁若去美国,她说:“我哪里走得开?你爸爸身后的事,10年也做不完。”
她独居后,近邻史佳成了她的“信使”之一。80年代初,史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经常看到文洁若来查资料。一般人来借书都要史佳帮忙找,但文洁若对这些资料了如指掌,都是自己直接查找。很多人为了方便复印,会把一本书拆开,她从来不会,而且每次还书都会给书包上新书皮。
史佳有时会帮文洁若传递稿子。文洁若每次都在黄昏时分来,因为这时日光下已看不清稿子,而天空又还微微亮着,她觉得这点阳光很宝贵。
多年来文洁若一直自己做饭,极其简单,只把食材统统倒进锅内用食用油和盐水煮,然后分成几份吃两天。她每周去饭馆吃一次鱼,打包回来再吃几顿。
2000年后,她年事渐高,表外甥黄友文成了她的一位助手。黄友文觉得,文洁若为人简单赤诚,很多人打着各种名义来家里搜罗资料和手稿,她都任其拿走。她还曾被人以建萧乾墓的名义骗走很多钱。
张斌说,文洁若向来不怕任何打击,她说损失一点钱没事,因为生命和健康最重要。“何况国家有补助,超过90岁的人每个月补助还多500块,何必为几十万揪心。”
《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南京市新华书店邀请她和《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等来签售,杨苡的女儿赵蘅第一次见到了文洁若。
赵蘅记得,与衣着朴素的母亲不同,文洁若穿了一条裙子,搭配大红色外套,还化了妆。
赵蘅说,虽然同为翻译家,但母亲杨苡与文洁若的性情完全不同。杨苡很会生活,兴趣广泛,童心未泯,而文洁若除了工作,再没有其他物质和享受的*。她觉得,文洁若的很多做派和生活哲学都与众不同,从不看别人的喜好行事,喜欢当众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虽历经坎坷,她身上找不到困惑、忧愁、苦涩与挣扎的字眼,精神状态总是像一个斗士,全无感伤,简单明了。
这些年赵蘅每次见到她,她总是信心满满地说,自己要赶上杨苡(杨苡已101岁了)。
她经常问赵蘅,出了几本书了,让她汗颜。
她没有三个子女在国外的电话,从不主动联系他们,也不想让他们常回国探望:“我还要忙自己的事呢,不要打扰我。”现在,她正应重庆出版社之邀翻译太宰治的《惜别》。
她一直独居,直到今年夏季摔了一跤,右手手腕骨裂,93岁的她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请了一位保姆。休息时她喜欢和保姆聊天,给她讲与萧乾的过去,讲儿时的旧事。
小时候,她家住北京东北城的桃条胡同3号。胡同不长,总共也就住了十来家人。她家住的是个大四合院,前后共四进,还有一个西院。母亲在五个院子里都种满了花,招来很多蜜蜂、蝴蝶和蜻蜓。文洁若原名文桐新,五姐妹的名字依次为桂、树、棣、檀、桐。院子里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们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根本不用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在书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