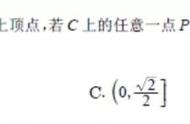文 | 王一方(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1如果说医学史是一部新知奇技的发明发现史、疾病疾苦的征服史、杰出医家的风光史,那么公共卫生史则是一部蒙难史,在疫病、慢病忧伤中反思、觉醒的彻悟史。时至今日,这种不对称仍然存在。
在现代医学的演进中,价值断裂的情形依然比比皆是,治疗与照护、技术与人文,尤以治疗与预防的疏离最为明显,教训也最深刻,100多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3年的新冠疫情,都有沉重的心灵叩击。
因此,要洞悉人类健康与人类疾苦的潮起潮落,并洞彻公共卫生的价值,离不开历史的景深、哲学的高度,以及社会学的视野与人类学的田野。卫生学泰斗、医学社会史先驱、美国医学史家乔治·罗森的著作《公共卫生史》就是一部充满智慧光辉的思想力作。
在防疫与控制慢病的历史认知上,人们交替使用“预防”与“公卫”两个核心词汇,两个概念各有侧重。预防医学是相对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是相对于个体医疗。随着历史事件的交叠刺激,人们逐渐意识到预防先于治疗,并高于治疗,必须下好先手棋;也明白了公共卫生大于、优于个体保健,需寻求系统的解决方案。
“卫生”的本义为保卫生命,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感的词汇。古往今来,卫生使命的延展路径很清晰,从热病到非热病,从急病到慢病,从传染病到非传染病,从疾苦到苦难,从疾病到健康维护。
在罗森笔下,早期的公卫人像侦探、像侦察兵、像人类学家,在传染病现场抽丝剥茧,探寻疾病的微观因果链条,捕捉“零号病人”,圈定传播源、传播途径,区隔易感人群。而现代的公卫人则像战略家、像将军、像卫星遥感器,用超视距、大象限、大数据探究人类(全球)健康、疾病,了解痛苦与死亡的宏观规律与发展趋势。
曾经在美国纽约卫生局效力多年的罗森极力推崇广义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包括政府公共卫生的管理部门、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机构、公共卫生学术机构。这些机构组织通过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群健康的目的。
因此,WHO(世界卫生组织)将公共卫生定义为“旨在为人们提供健康生存的条件的活动,关注人群,而非单个患者或单种疾病”。
2在罗森的公共卫生历史叙事中,最初的公共卫生观来自宗教戒律,把禁食猪肉的宗教信条看作是早期公共卫生立法行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宗教和巫术的混合体。
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病因和预防的超自然观,并逐步用理性的科学方式向自然界寻求病因。随着自然病因观被人们接受,并受益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秩序和清洁的重视,德国科学家科赫、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显微镜下的发现使公共卫生的脚步迈入现代微生物分析的语境,然而,自然主义的余温与启示仍在,不可轻易抹去。
历史叙事最忌平铺直叙,因此,罗森没有驻足流连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传统的自然主义健康观、疗愈观,而是揭开了罗马帝国的惨烈伤疤。罗马帝国纵然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国力强盛、生活富足,最早发明了完备的城市给排水体系,但是接二连三的征战与伴生的瘟疫,成为罗马帝国崩塌的导火线。
据古罗马学者塔西佗《编年史》记载,在公元65年和公元165年,罗马帝国分别遭受两次瘟疫的重创,第一次“罗马城内,死亡迅速蔓延到各个阶级”,第二次以“安东尼大瘟疫”被史家记载。此疫之后,罗马帝国由盛转衰。
历史在瘟疫的刀锋上行走了2000年,一直到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公共卫生才被认定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1848年,法国医师盖林首次提出社会医学概念,19世纪后半叶,细菌学的发展使有些医学家仅重视生物病原体的致病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社会医学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
在罗森看来,19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公共卫生发展的重要分水岭,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概念逐渐形成。
1834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标志着有组织的、政府主导的现代公共卫生时期的到来。参与起草法案的Chadwick在后续的执行调查报告中强调了“卫生状况”的重要性,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于1848年出台。这是人类第一次为保障公民的健康进行立法。
19世纪早期,公共卫生措施主要集中在清洁环境、改水改厕上。到了19世纪后叶,宏观视野中的统计资料已开始在控制疾病中发挥作用,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和应用,奠定了今天流行病学和循证公共卫生学的基础。
为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对人群健康进行定量观察,公共卫生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主题。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之父”格兰特就研究了死亡分布及其规律。18世纪,法国的路易斯开始进行疾病分类;英国统计学家、现代流行病学创始人法尔开创了有关患病率、死亡率、疾病与死亡原因的统计研究;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标志着科学的主动免疫的开始。
到了19世纪有关研究加速发展,英国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在伦敦进行霍乱调查,标志着流行病学中现场调查、分析和控制方法的产生;同时期,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发展为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群健康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斯德建立了微生物学理论,使得后续在烈性传染病预防控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成为可能。
公共卫生逐渐发展衍生出了包括预防控制传染病、环境卫生、职业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妇幼和青少年卫生在内的一整套系统理论、方法和干预措施。
3众所周知,细菌和病毒是微生物界的两大主要阵营,进入20世纪,人们逐步掌握了细菌性疾病的防治方法,病毒性传染病随后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的首要疾病。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很多病毒性疾病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造成5亿~10亿人被感染、5000万~1亿人死亡。看似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每年仍会导致300万~500万重症病例、25万~65万人死亡。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到了1928年,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具有抗菌作用。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伤员急需抗感染治疗,青霉素得以工业化量产。这挽救了大批的生命,也拉开了人类抵御感染性疾病的大幕。
1943年,美国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实验室的博士生阿尔伯特·沙茨、伊丽莎白·布吉首次分离出链霉素。它是治疗肺结核(TB)的第一种抗生素。1952年,瓦克斯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链霉素的使用,抗药的结核杆菌也随之出现。1965年,利福平的发现使结核病的治疗实现了一次更大的飞跃。随后出现的用于治疗结核病的抗生素有吡嗪酰胺、乙胺丁醇、链霉素、异烟肼等。
然而人类面临的事实是,耐药菌株不停地产生。大约1/4的世界人口已经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每年约有1%的人口出现新的感染。
英国流行病学家托马斯·麦基翁曾指出,“链霉素治疗自1948年至1971年被引入以来,将死亡人数减少了51%”。在链霉素和卡介苗疫苗普及之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结核病死亡率已经下降了90%至95%。也就是说,抗生素对结核病死亡率下降的贡献实际上非常小。
罗森身后近50年间,医疗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疾病谱重新排序,死亡率持续下降。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疾病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
从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来看,传染性疾病的死亡威胁不断减少,慢性病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控制慢病、延长预期寿命显得越发重要。当今的肿瘤新药能激发、调动机体免疫系统,有效抑制癌细胞。人们有理由相信,癌症“不可治愈”的帽子不久就会被摘掉。
预防医学更重要的转变是健康促进的多元化、立体化、深入化,立足于公众理解医学、健康、疾苦,塑造全新的生命观、健康观、疾苦观、医疗观,医者从医学知识传播到健康智慧导入、从技术介入到教育性干预,包含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以及生死辅导。从“患者至上”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如此大的变化,罗森九泉有知,想必也会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