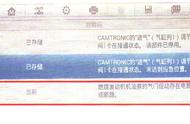在我心中,有两个月亮。
一个是现实生活中所在城市的月亮,一个是故乡的月亮。
“月是故乡明”。无论走到哪里,故乡的月亮总是让人眷恋。
城市里高楼大厦、灯光璀璨,即使是月圆之夜,也很难看到它的真容;故乡山高水长、村落稀疏,只要小小的月牙儿一露脸,就能看到她的倩影。
心里总有种感觉,城市里看到的月亮很遥远,与自己陌生而冷淡;故乡的月亮很亲近,与自己熟悉而温暖。
记忆中,在故乡生活的岁月里,有三次见到的月亮很难忘。
第一次是在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寨子里的人们经常把自己种的时鲜蔬菜挑到街上去卖,当时没有车辆,乡亲们也没有养骡马的,所以赶街上城都是步行。因为集市距离寨子较远,大概有五、六公里的样子,所以每到街天,乡亲们都是半夜起床,打起手电筒挑起担子便走。那时候母亲年轻能干,每次上街卖菜她都要和父亲各挑一担,一来是走夜路做伴,二来是减轻父亲的负担。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母亲便让我和她做伴去。那天应该是农历冬月的下半月,天气很冷,霜水很大,黎明前的月亮仿佛一个洁白的玉盘挂在天空,将乡间的小路洒满银辉。人们不用照明工具,就可以挑着担子在小路上奔走。我跟在母亲后面,看见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挑着担子行走,步子慢了不行,必须要小跑才更省力。因此,我总是跟不上母亲的步伐,只好走一段跑一段,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母亲说着话。坐下歇气时,月光将母亲脸上的汗珠映射得晶莹剔透,我忽然觉得月光下的母亲有一种朦胧的美,仿佛天空中彩云绕月的朦胧美。此时,我觉得天上的月亮比任何时候都美丽。母亲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把我拉进她怀里,轻轻地吟唱:“月亮堂堂,打发梅香;梅香告状,告着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洒水,洒着小鬼;小鬼劈柴,劈着老怪;老怪切菜,切着蛤蚧……”从此,我记住了“月亮堂堂”这个词,每每看到月圆中天,都会不自觉地吟起这几句歌谣。
第二次印象深刻地记住故乡的月亮,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那是花儿时常在梦中绽放而青春萌动的恋爱时节,我收到了远在百里之外的女朋友的来信,读着情人的喃喃细语,思念如芳草,在心的角落里疯长。我趴在小阁楼的窗台上,看着一轮皎洁的明月从东边的山峦间徐徐升起,想到美丽多情的她此时此刻正与我同望一轮明月,不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含着一枚青橄榄,酸酸的、甜甜的。仿佛天边的星光,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难免终夜相思,彻夜不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正合此时的心境。新月初升时,给人的感觉是庞大而明亮,里面忽隐忽现的几个轮廓,仿佛就是嫦娥、桂花与小白兔,十分引人遐思。清辉透过云层,朦朦胧胧地照进房间,为我披上一件梦的衣裳。光阴绰约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清香。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月亮缓慢地行走,心情却如潮水般涌动。月挂中天的时候,玉兔儿睡了,人间只剩蟋蟀的歌唱和我的思念。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激起心海无尽的波澜。明月千里,相思无岸。这种相思,就像饮酒,少了,不够爽;多了,又迷茫。此刻,我相信,最能理解我的心境、最能默默无语地陪伴我的就是那轮明月了,她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海里。
第三次印象深刻地记住月亮是娶妻成家后。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和年轻秀美的妻子凌晨5点起床,挑着一担自己种的蔬菜到四公里外的集市去卖,我们走在沙石公路上,“唰唰”的脚步声在月光和清风中很有节奏感,而且很响亮。妻子边走边看月亮,一边与我说着话,不让我累着。因为到集市的路有两公里是荒郊野外,没有村寨,而且不远处还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地,我担心妻子害怕,就背诵一些关于月亮的“歪诗”和顺口溜来增加“热闹”的气氛。当我念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板脏;举头拍蚊子,低头踩蟑螂”时,逗得妻子大笑起来,银铃般的笑声在如水的月光中传得很远。当我念出“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个圆盘,有时像把镰刀”的谜语时,妻子若有所思地看看月亮说:“这不是小儿科嘛,早在读小学时就学过了!”我们在月光下愉快地行走,虽然肩上挑着担子,却不觉得累。黎明前的月色更易使人产生一些朦朦胧胧的情愫,犹如那月旁淡淡的白云,若即若离,惹出一缕缕空灵的诗思。有一种无形的牵挂如微微的秋风轻拂,清清淡淡的凉;还有一种成熟的思恋如秋雨轻抚,丝丝缕缕的爽。为了幸福生活奔忙,谁能轻易放弃一个沉甸甸的秋天和那美轮美奂的月光呢?
这么多年来,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时光如流水悄悄逝去。无论在农村、在城市,或是在家中、在野外、抑或是在旅途,不知看到月亮多少次,但是印象都不深刻,只有这三次是终生难忘的。细细想来,我之所以记住这几次的月亮,都是与女人有关,她们是母亲、妻子,她们都是勤劳善良的贤妻良母,而且她们与月亮一样都有一种清淡而又温暖的阴柔之美。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份深深的、浓浓的、扯不断的情感牵系,因着这种牵系,便含着笑,怀着一种感激与美好,在心灵深处烙上了一份难以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