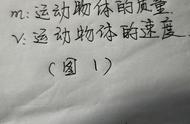底层百姓大多天性喜爱热闹,很多人嫌昆曲冷清难懂,所以听到其他戏班唱昆曲,“便哄然散去”。但这些底层观众却被徽班的多声腔吸引,剧场气氛相当热烈,出现了“肩摩膝促,笑语沸腾。”的景象。这是徽班“联络五方之音”的结果,没想到也联络了观众的心。
徽班在声腔上的兼包并容 ,也表现在人才吸纳的开放上 。只要是有特长的演员,均可加入徽班,并不因为籍贯而受到歧视。 徽班长期坚持联络五方之音,出名的艺人高朗亭、邱玉官、江金官、 苏小三等等,都是“昆乱俱妙”,又能“跌扑矫健自由”。很多徽班演员学书习画,并将书画才能用于戏剧中。春台班的名伶范秀兰演《马湘君画兰》时,当场“洒翰如飞,烟条雨叶 ,淋漓 绢素”,引起观众的轰动。
徽班演的兼容并包,得力于徽商的支持。 明、清徽商豪富,戏曲是他们援结豪贵的一种手段。 徽商对待各种戏曲声腔比较开放,既把昆曲奉为雅部,又不排斥花部诸腔等地方戏。 两淮盐务总商江鹤亭从事盐务四十年,“凡抵候南巡者六,祝皇太后万寿者三”,深得乾隆宠信。 他从北京延请名伶魏长生南下,对扩大花部的社会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原来扬州皆重昆腔,外地的梆子腔、 二簧调、 高腔等只能在城外四乡演唱,自江鹤亭延请魏长生组织春台班后,大大的提高了花部的地位。 花部诸腔中来自安庆的二簧调很快为春台班吸收,形成“花”、“雅”声腔并蓄的新特点。

乾隆八十大寿时,进京祝寿的徽班多为昆腔班,而昆腔又多雅静, 所以进京的徽班都准备了花、雅两部数出大戏,做到有“花”也有“雅”。春台班、三庆班既能唱二黄腔、京腔、秦腔,也能唱昆腔折子戏。所以有人说三庆班等戏班是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而入京的。如无 “戏艺”,自然无法在京城立足。
京剧的主要声腔是西皮、二黄,可以肯定的是,西皮二黄是由徽班带到北京的,但西皮二黄并非产于徽州。 西皮是秦腔演变为襄阳腔而成,湖北人称为“皮”,“西皮”的意思是从西边传来的唱腔。 二黄源于黄陂、黄冈、黄安一带,由弋阳流传到安徽后演变为四平腔,再由四平腔演变发展而来。湖北的黄陂、黄冈、黄安与安徽的安庆、徽州以及,江西的弋阳相距不远,“西皮、二黄”是三个省份戏曲唱腔综合吸收和发展的产物,并由徽班艺人带到北京,流传到全国各地。
由于进京徽班吸收了昆腔、秦腔和扬州乱弹等艺的术,并经过变化吸收,使进京的徽班唱腔日趋完臻,最终成为一种昆、乱兼备,诸腔杂陈的演出团体。虽然乾隆时刚进北京的徽班主要唱的是“乱弹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嘉庆以后, 徽班不少演员便以擅唱昆、乱两腔而著名。

“ 乱”是 “乱弹腔”的简称,腔调以 “安庆二黄” 为主,并在许多地方借鉴了“扬州乱弹”的表现形式,其声腔分为以笛伴奏的 “吹腔 ” 和以月琴伴奏的“秦腔”两种,也叫作 “梆子乱弹腔” 。扬州乱弹腔和陕西的秦腔同出一源,都以月琴为主奏乐器。 徽班能在北京取得成功,没有江苏的昆腔和扬州乱弹的配合,是难以实现的。
徽班的唱腔在嘉庆年间逐渐形成一致,基本上各种声腔可以同台演出。对于徽班来说,皮、簧结合有两个阶段: 一是徽、秦合流 ,二是徽、 汉合流 。徽班进京之初,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为主,这种改进后的吹腔被北京观众称作“新出秦腔”。吹腔本用笛子伴奏,徽班在嘉庆年间把它改用胡琴伴奏,其唱腔风格逐渐柔媚低回,形成了一种新的“徽调”,又可称为“汉调”。这一重大转化,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班曰徽班,调曰汉调”。

这种汉调新声很快在徽班中流行开来 ,因为它是对来自徽、 秦声腔的一种改造,同徽班所唱的曲调属于同源异流, 所以演员们改调并不困难。 此后, 徽班艺人对其进行了一番综合溶化, 使二簧腔和西皮腔都能以丰富的板式、优美的旋律成为主要演唱曲调 , 并达到风格上的既有二黄深沉柔和与西皮刚劲明快的强烈对比,又能做到可以在一剧中合用的和谐统一,基本完成了曲调的定型。
选择皮、簧为主并不是形成京剧的唯一标志。 皮、簧流布甚广,京剧能同它们区别开来,是因为在表演过程中皮、簧的京韵化。 字音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原本南方来的徽班唱起二簧时,尚吴楚之音;但为了适应北京的市场,“悦京师之耳,故概用京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