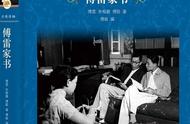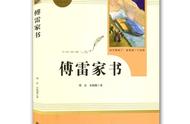1948年,傅雷一家人搬到了云南昆明,国际上甘地遭刺*,傅雷为了这事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朱梅馥流着眼泪,敲起书房的门说:“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在昆明,十四岁的傅聪也迎来了叛逆期,和傅雷闹起反抗,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傅雷索性不管他,交代好昆明的老朋友之后,把傅聪一个人丢在了昆明,自己和朱梅馥、傅敏回上海了。
在昆明上中学时,傅聪不服从教官管教,整天逃课谈恋爱、打桥牌,很快被开除。傅聪只能换一个学校上学,但每换一个学校,过不了多久校方都会因为傅聪不务正业把他开除。
直到傅聪跟着同学一起考云南大学,误打误撞考上后,他才逐渐开始醒悟。
在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在唱诗班给同学们伴奏了一场音乐会,傅聪收到一封解放军听众写的信,里面包着一枚长征纪念章。信里写着: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傅聪>
傅聪非常感动,十七岁的他觉得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度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筹齐路费,一个人从昆明步行一个月回到上海。
傅雷看到走回家的傅聪,觉得儿子长大了,他认为傅聪很有骨气,也能把音乐学好。
那时起,傅雷和傅聪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硬。
为了把之前落下的钢琴给补回来,傅聪每天苦练八小时钢琴。1952年,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18岁的他第一次登台就吸引了上海音乐节的注意,被选送参加1953年夏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

1954年1月17日,傅雷、朱梅馥、傅敏一起到上海北站送傅聪上北京,火车远去,家人还站在月台上望着傅聪远去的火车。
后来,傅雷开始给傅聪写信。他给傅聪写的第一封家书,是一封道歉信:“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脑袋。”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
那一年,傅雷四十岁。

<傅雷与傅聪>
此后傅雷给傅聪的信中,写得更多的是傅聪自己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例如:
傅聪到了别人家进了屋子,脱了大衣,会忘记摘掉脖子上的丝巾,傅雷让他必须把丝巾和大衣一起脱到衣帽间;
傅聪常常把手插到上衣口袋处,或是裤袋里,傅雷认为不符合西洋礼节,让他不要把手插进上衣袋里;
傅聪弹琴时会摇晃身子,傅雷觉得这种动作会影响听众们的注意力,让他戒掉摇头晃脑的习惯。
类似的“小毛病”,傅雷写了非常多。《傅雷家书》中,傅雷给傅聪写了一百七十七封信,大概三十五万字。而傅聪写给傅雷的回信却只有六封,且都很类似:
他一般会先说自己很久没有写信了,然后再为自己很久没有回信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就像这样:“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的。”
这让傅雷心生不满,他给儿子写信:“我们历来向你讨家信,就像讨债一般。你该多了解你爸爸的脾气,别为了写信的事叫他多受屈辱,好不好?”
“做爸爸的不要求你什么,只要求你多写信,为了你对爸爸的爱,难道办不到吗?”
傅聪对父亲感到抱歉,但却又无力分身:“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父亲这样的反应。我要是再多写一点,那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