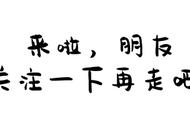来源:广州日报
很少有人知道,
广州荔湾区明心路有一间盲人大院。
2018年底,
因白鹅潭建设需要,盲人大院征拆,
48名视障人士迁入西村街道和苑社区。
和苑社区
本是一个大型拆迁安置社区,
如今也成为这群特殊街坊的安居之所。
近五年过去,
他们有没有适应新环境,
各自又有着怎样的过去?
带着这样的好奇,
记者走进和苑,聆听他们的故事。
她,幼年患退行性眼病
如常人般奋斗至中年
视障愈来愈严重
慢慢看不见了 “我决定跑起来”
人物档案
陈惠兴,幼年即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视力慢慢减退。仍然靠个人努力考上师范学院,成为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视力越来越差以后,选择“跑马”“看”世界。

“正前方一团亮光,应该是天空,右边竖着的阴影,在抬头60度的位置结束,应该是楼房没错了。”
在陌生人看来,陈惠兴的眼睛是睁着的,与常人无异,可她什么也看不清。即使在生活了5年的社区周边,“看见”仍要靠推理。
2018年底刚搬来荔湾区和苑社区时,她对环境很不熟悉,只能隐约看见路中间的那条白色分隔线,盯住这条线,才能把路走下去。有时候盯错了,误把两边白线当中间线,跌倒、撞人时有发生。
世界越来越模糊
从她三四岁起,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病就像阴云笼罩在头顶。
1967年陈惠兴出生在芳村盲人大院,出生时父母双盲,小时候她是父母的“小拐杖”,“他们总说我带路不看路,其实是看不清,家人带我去看眼科,一查,视网膜色素变性。”父亲同样患有这种眼病,母亲是后天致盲,作为女儿的陈惠兴没能逃脱遗传的大概率。

这是一种遗传性退行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加,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会逐渐退化,且无法再生。退行性病变是漫长的、渐进的,裸眼视力0.2、矫正视力0.4,是陈惠兴这辈子的视力“巅峰”,而后视力渐渐减退、视域慢慢变窄,最后,曾经看得见的世界消失在眼前。
这片阴云没能遮住陈惠兴的光。用只能看到5米以内轮廓的眼睛,陈惠兴在市八中(今培英中学)读完中学。
初三时,家人认为她的眼睛“大限”将至,“你爸爸就是20岁看不见的,不要考高中了,珍惜能看见的时候,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
面对这样的劝说,陈惠兴不服气,她理科学得比正常同学还要好,立志要当一名老师。她不仅考上了高中,还顺利考入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广州119中学(今花地中学)教数学。
板书写着写着就会歪斜,但这没什么妨碍,第一次带初三,陈惠兴把全班数学平均分拉高了40分。三尺讲台,她发光发热,与常人同样精彩。
“大限”始终要来。有人说,后天失明,是从一种世界进入另一种世界,而中间必须穿过的地带,叫做地狱。陈惠兴从小就有心理准备,她不恐惧,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她还是有点招架不住。
“我这个样子,别人看不出来,麻烦不少。”陈惠兴说,她40多岁时,总会不小心踢到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被误解心存故意。2015年夏天,她遭遇了一场车祸,拿着盲杖的她被撞到鼻骨碎裂,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那之后有了心理阴影,陈惠兴好一阵子不敢出门。休养3个月后,重返校园时,校方问她“还能不能继续工作?”她有些彷徨。
他们愿意陪我跑
当一扇门要关上时,陈惠兴用“跑”开了一扇窗。2015年10月,她接触到一个跑友团,决定用跑步来克服心理障碍、重拾信心。走路都有问题,怎么跑?所幸,有一群视力正常的跑友志愿当视障跑友的陪跑员。

在他们的陪伴下,陈惠兴在2015年完成了佛山西樵山半马公益跑;2016年3月广州组织10公里折返跑,陈惠兴拿到人生第一个完赛奖牌;2017年,她跑出国门,参加泰国清迈半马;2018年,陈惠兴挑战了广州全马。
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厦门、贵阳……5年来,国内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都有她的身影,奖牌已攒了40多块,最好的全马成绩是4小时27分11秒。
“每次跑到25公里后,都是咬牙在撑的,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跑?但每次跑完下次还会去报名。”陈惠兴跑上了瘾,3月26日,她又跑完了安徽芜湖全马。
各地打卡马拉松赛事,也是在看世界,这是她的另一个梦想。大学时,陈惠兴没有向同学们提起自己的眼疾,尽量同他们一样参与课外活动。大三那年的九寨沟之行让她至今难忘,黄龙五彩斑斓的土,九寨沟清澈见底的水,就连第一次经历的川西的高反,都深深打动着她——看世界是这么美好!
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说,“请善用你的双眼吧,就好像你明天就要惨遭失明之痛一样。”陈惠兴一生都在这样的预言下生活,却用这种紧迫感活出精彩人生。
跑完“芜湖马”的这几天,陈惠兴到黄山、杭州、乌镇转了一趟,朋友圈里,她在油菜花前笑得灿烂,“有生之年,在我能看见的时候,我要跑遍世界,看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就算完全看不到了,只要有人带,我都要去。”
他,少年颠沛流离
“广州给我一个家”
70年前漂到广州
“我现在91岁了”
人物档案
刘树光,今年91岁,幼年失明。1951年来到广州芳村盲人院,安家落户娶妻生女,5年前搬至荔湾区和苑社区,在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得以安居,晚年温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