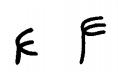图4 绥德墓门右立柱石拓片及其局部
李发林先生曾总结骑羊图像的画像石,认为其在山东常见,如在邹县下黄路屯、济宁城南张村、嘉祥、临沂白庄等地都有发现;当这类图像与神兽仙人等相组合时,其含义应与神灵相关。
汉代青铜摇钱树的陶座上,也往往塑有乘羊图像。青铜钱树是汉墓中的一种明器,主要分布于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汉中,乃至甘肃武威、甘谷、宁夏固原、青海大通、乐都等地区,也有流失到海外的;其流行时段可至东汉早期持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寓意为墓主人提供财富、保护其升仙以及保佑其子孙繁荣昌盛。钱树树座多为陶制,塑有仙人、神兽等仙界形象,或狩猎、庖厨、乐舞等人间画面。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就收藏有两件刻羽人乘羊的陶制树座,其形制相仿:底座皆由泥质红陶雕刻,上小下大,呈覆钟状,上部圆雕一羽人骑在一翼羊身上,羽人怀抱圆柱插座,大耳,面带微笑,肩生双翼,半裸穿着半身裙;翼羊带角、长须,翘尾挺立,腹下还有一只小羊在吮吸奶汁。
(三)羊首图像
山东还有一种刻羊首图像的画像石,也与神话题材相关。这类图像多见于门楣画像石上,多为一个羊首居中,也有两或三个羊首在画面上左右平均分布的,周围夹带着其他造型各异的神兽。
如济南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墓门横额石的正面(图5),居中高浮雕一正面羊首,头顶硕大的双角分别于左右侧向下翻卷、造型优美,羊面部五官清晰、神态安详;其两侧分别为青龙、白虎。青龙在东侧,昂首向前,龙首前、后各有一仙人,龙爪前还有一飞鸟;白虎在西侧,回首后望,一仙人乘坐白虎身上、手持虎尾,白虎后刻一飞鸟,画面背景装饰着云气纹。这种与仙人神兽相组合的羊首,也应与神仙世界有着密切联系。
图5 济南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墓门横额石
羊首除了出现在画像石上,还可能被雕刻在金属饰物上。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羊首饰件,宽4厘米、高3.8厘米,雕一正面羊首形象,双角也自头顶向左右两方垂下、角尖卷翘,尽显雍容之气派(图6)。也有的金饰件上并列雕刻双羊首,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8件羊首纹金饰片,它们原为缀在南越王丝巾面罩上的装饰品。每件金片上各雕有两个相背的侧面羊首,每个羊首显示一个尖角,也自上垂下、角尖卷翘(图7)。

图6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羊首饰件

图7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羊首纹金饰片
在金属上刻动物图像,多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本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受其影响,羊首纹金饰即属其产物。如斯基泰文化中的一件双羊铜器,上塑双羊首,头顶双角长而向后弯曲;颈项以下各伸出一扇羽翼、分别向左右展开,羽翼由数条长条形羽毛组成、翼尖向上微卷,线条简洁而明快,造型刚健、充满力度,又因流畅的弧线而被赋予了柔韧与弹性(图8)。

图8 斯基泰文化双羊铜器
羊为什么能够成为神兽?
羊在汉代作为神兽,其形象被刻画在形形色色的器物,如画像石、画像砖、陶制明器、金饰、铜器等上。图像的分布地区基本覆盖汉代帝国的领域,流行时段也贯穿了两汉。
神话动物的造型取材于现实生活,其手段往往是在现实动物的基础上加以想象性元素、赋予其神力,能被化用的现实动物身上往往具备可被神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是外型上的出尘奇特,也可以是精神内涵上的契合。就羊来说,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兽,且其图像的流行能有如此盛况,既与现实的生活生产条件紧密相关,也离不开当时人对羊的主观认识与想象。
透过神羊这一图像,我们能够贴近汉代社会的现实,也能够了解当时人们的造神逻辑。
(一)现实生活的基础
羊在外型生理上具有丰满、绵柔的特征,给人以安详、和美、端庄之感。《说文·羊部》:“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徐铉注曰:“羊大则美,故从大。”另外,羊的肉鲜美,经驯化,它还能承担一定程度的重力,可用作出行或农作的工具,这些特性都有益于人类生存,所以人们将之驯养以改善生活条件。
在先秦时期,羊就已被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汉代延续了这些风俗。羊常被描绘在画像石上的庖厨、狩猎、车骑、甚至乐舞中的建鼓图像中,还有一类专门表现牧羊的图像,更是栩栩如生地描摹了汉代养殖羊群的情境,这类画像石在山东、陕西绥德多见,应是当地畜牧业与经济发达的写照。
如榆林横山孙家园子墓墓室门楣石的图像,充满生活化情趣(图9)。画面右方自左向右刻有牧牛、牧羊及相马图,其中的牧羊图中,左侧有一羊站立,后蹲一人俯首挤奶。右侧立一人,面向一群朝他奔跃而立的羊,羊的姿态各异,或前蹄顿地、后蹄扬起,形容其急速奔跑的动态;或四肢立地缓步向前;格外有趣的是居中、正面对牧羊人的一只大羊,它低头埋于胸前,弓起身子凸出后背,臀部的重心向后,四肢立地但皆向后倾,在它的后背上挺立一只小羊,应是子母图像的写照。大羊如此奋力相抵的情态,与其背上小羊的天真盎然形成对比,可能正突显出大羊对小羊的爱护之意。画面形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家畜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