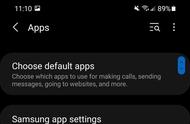许三多以近乎“苛刻”的纪律践行着军人的优良作风坚守着他视为真理的信念,但他却并没有感觉到外界的束缚,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明明身处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部队,却拥有了其他人都没有的“自由”。而与此同时,许三多完成了从信念到信仰的转化。
这种信仰并不单纯是情感上的盲目,而是对“知识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正确性”的内在坚信、确信,以客观规律泊知识为基础,与宗教信仰完全对立”。由此可见,许三多的信仰都是自身实践经历所总结得出的结论,由此所转化而来的每一实践活动的具体目的和具体方法在本质上都是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一致的。
从草原五班重回到钢七连,许三多做事情的方式变了,不再是单纯的用过去经历来判断,更多的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对史今的,钢七连的,伍六一的。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部队的生活已经让他走出了父亲“否形式”教育的阴影,一直到后来父亲让他复员没有成功才体现出来,但见证许三多成长过程的战友看出来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开始用自己的思考来做事情,当他得知自己的军事训练成绩会决定班长的去留,他不再盯着自身的弱点,而是把每一个小目标都当救命稻草一样抓着,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他已经成为了让人仰望的参天大树了。
所以许三多破全连记录的三百三十三个腹部绕杠,是他所有过往积累到顶点的一个爆发,也是量变带来的质变,这也意味着许三多和全连公认的“孬兵”作了最后的告别。

单纯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给了许三多精神的自由。很多战友早早地就丧失了这种天赋,因为很聪明,又擅长自作聪明,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五班那群人中,最聪明的当属李梦。可多年的驻守,早就让他丢失了信念。那本没有写出来的小说,成为了他仅剩的寄托与遮羞布。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是的自我感动。这句话暴露出的实际问题是,有时击败我们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对困难的想象。许三多一直念叨着那句“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在进入七连之前,他没找到;在史今复员时,他也没找到;在七连整编之后,他依旧没找到,归根到底,许三多并没有完成主体的建构。
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建构是通过《俄狄浦斯》中的弑父情结完成的。在该剧中,许多人物都与主角许三多组成了“父子关系”,主要关系有许百顺与许三多、老马与许三多、史今与许三多、高城与许三多、袁朗与许三多。
而这些“父子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士兵突击》中“父亲”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予爱和帮助的,以老马、史今为代表;一类是给予规训与惩罚的,以许百顺、高城为代表;而袁朗是二者的综合,既有帮助的一面,又有规训的一面。无论是给予爱和帮助,还是给予规训与惩罚,最终的作用都是一致的,即将许三多纳入到社会秩序中来,完成对他的主体建构。

其实,史今招许三多入伍时,明确提出许父以后不再叫他“龟儿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更名或过继,就已经表明了许三多身份开始改变。相比老马、史今,第二类“精神之父”对许三多主要以打骂、讽刺和批评为主。
生父许百顺试图仅靠这种训诫形式来让其成为社会规范中所认可的角色,但并没有成功。高城对待许三多主要以批评惩罚的形式为主,从一开始让其抄写保密手册,到将其流放到五班,都是对许三多的暴力否定,甚至放弃将 其纳入规范之中,使得主人公内心充满焦虑。直到最后,高城帮助许三多解决了心理问题,才表现出作为父亲关怀的一面,使得这个精神之父更为称职。
“作为父亲严厉的一面,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惩戒不合规范的‘子’,使其符合父法的秩序,并最终纳入到秩序中来。他们是主人公产生焦虑的原因,但也是激发主人公战胜焦虑的动力。意识形态强化了严父使得‘子’成长的作用,也遮蔽了对‘子’的专横与暴力,这一正面的凸显也使得受众认同这一惩戒方式,并将其视 为建构主体、解决意识形态焦虑的途径。”
团长说:“在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两个字,叫做到。”许三多的幸运是,走着走着就找到了意义。而更多人的不幸,则在于勤于思索意义,在行动上反复纠结,没完没了地寻求安慰,最终却被困在原地。

所以许三多对自己要求最严格,这种外人看来近乎“变态”的自律促成了许三多完成主体的建构,成为了精神最自由的人。许三多并没有察觉到大环境的束缚,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去行动,他的“自我意志”与军营的要求高度统一,因此也可说许三多是军营中行为约束的自由者。
内容来源*佛系老兵,头条可能无法及时回复,有问题咨询的朋友欢迎到公众号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