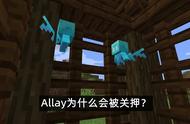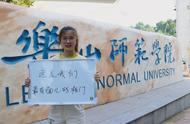“我搬到这儿已经四十年,你一定听说过我的事。
我丈夫在有名的公司上班,人们最喜欢议论他和秘书鬼混的事。他们确实去过酒店,还挺上档次。”门房自轻地笑笑。

“后来我老公开始拿公家的钱,他们俩逃到了南美洲。”门房把酒一饮而尽:
“不久,有人上门来告诉我:‘您丈夫去世了。死于车祸,在南美洲。’
我的生活从此停止了。

我姓华莱士,与供人饮用的华莱士喷泉同名,所以你看看,我注定一生与眼泪相伴。”
艾米丽偷偷看她的表情,她一定还爱着她的丈夫。
这是一段无止境的憎恨,而这,源于曾至死不渝的爱。

门房翻出她丈夫变心前寄的信,那些回忆依然温热:
【亲爱的玛朵,我夜不能寐,食不下咽。
我坚信自己,把此生唯一的寄托留在了巴黎。
只有等到星期五下午3点我才能见到你,看到我的小可爱穿着蓝色的吊带裙,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
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