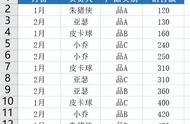作者:张义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过去以疾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再次获得人们的关注,观众仿佛要从艺术中勘探现实,寻求自我的救赎。《传染病》是美国导演索德伯格2011年执导的作品,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就叙事内容而言,虽然该片具有与当下极其相似的现实同构性,但电影首先是艺术,因此,对该片的艺术读解是关照现实的逻辑起点。

《传染病》海报
疾病的隐喻
在艺术作品中,创作者有时会借由描写某种疾病的传播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判断。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指出,“作为生理学层面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因此,疾病身份的多重性是其既能作为叙事元素,又可以隐喻现实的基础。不同于《我不是药神》对现实的人文关切,《传染病》更多的是影片的“自我隐喻”,即以影片内的疾病隐喻影片的故事,实现一种文本的自足性。
首先是疾病“无名”的隐喻。影片中,从开篇至结尾都没有对传染病及其致病病毒有明确称呼,直接跳转至症状的描述,这种处理手法一方面在叙事上塑造病毒的未知性,为电影增加悬疑感与恐惧感,另一方面则是隐喻了影片中几组人物的道德污点。开篇中第一个感染者贝丝,本是育有儿女的成功的中产阶级女性,但在抽丝剥茧的叙事中,观众借由其丈夫之口逐渐得知她与情人曾有过长达6个月的感情暧昧;阴谋论记者艾伦趁疾病爆发之际散布不实消息,以牟取暴利;艾伦的被捕则是在医生的“虚伪掩饰”下的诱捕;疾控中心负责人埃利斯•切弗以蒙骗、威胁的方式扣押外援专家的香港医生……几乎在每个人物光鲜正面的形象下都藏纳着道德污点,污点的存在让其无法获得正向的道德命名,有如无名的病毒一般。
其次,疾病传播的无序性也隐喻了影片中社会的混乱。正常而言,疾病因其不可控而呈现为无序状态,人类社会由于有完整的规则秩序,往往可以对进入秩序内的事物实现同一化,但影片中疾病爆发后,社会系统并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反应链条,也没有有序有效地减少疾病带来的影响,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增生了更多的混乱。影片中,这种混乱在众多普通人身上体现为对生活物资、医疗物资的迫切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抢购甚至抢劫;在一些医疗系统体现为对病毒检测程序与规定的僭越,比如在接到结束检测命令后的三级实验室医生,仍出于私心没有将病毒销毁;在政府系统体现为对是否如实公布疾病传染情况的争论……当然这与病毒分不开,但病毒的出现恰恰考验的是社会承受能力,倘若说是病毒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不如说社会本身已经存在混乱的“温床”,恰如病毒传播的无序形式一样。

《传染病》剧照
反类型叙事
反类型叙事是相对类型叙事而言的。类型叙事是指电影作品按照一定的类型程式进行故事的讲述,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反类型叙事就是对规则的突破,其本身难以归类。《传染病》是以疾病为题材的电影,但相对于其他电影作品中的疾病而言,本片的疾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导致在表现范围上很难集中在某个患者身上,也就无法按照传统类型中以某个主人公为叙事承担者的方式讲述故事。因此,本片的反类型叙事首先在于打破单一主人公的叙事模式。
具体而言,影片设计了贝丝一家、疾控中心多名医生、支援香港的专家、记者艾伦等多组群像,每一组中又有主要的叙事承担者推进人物关系的发展。事实上,这种叙事手法是费力不讨好的,大量的人物角色分解、削弱了故事的戏剧性,同时也较难让观众理出头绪,但这恰恰是导演索德伯格的高明之处,将代表不同群体的人物同时划归到传染病的背景下,描绘出一幅疾病肆虐下的众生相:贝丝的丈夫托马斯如何保护自己的女儿;医生凯特•温斯莱特面对未知的病毒,是怎样的勇气让她选择将自己作为疫苗的实验对象;支援香港的专家在遭受蒙骗与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仍呵护着村里的孩子;而记者艾伦又是如何为牟取暴利不惜编造、散布谎言……面对传染病,不同的人物表现出不同的选择,避免了类型叙事“人为雕刻”的痕迹。
其次,导演在叙事形式上也拒绝类型叙事,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的设置和情节的编排上。影片的叙事结构类似于“章节体”叙事,即场景间的切换往往会以字幕形式标记时间和地点,如开头就是“疾病爆发第2天”,然后讲述这一天第一个患者贝丝的患病,随着疾病蔓延,时间切换的跨度越来越大,同时具有标示性的地点也成为切换的形式,往往以“××城市,人口:××万”为样式,制造出一种“新闻式”的影像,给人一种疾病在全世界传播的真实感。
另外,在结尾情节的编排中,导演以反类型的叙事手法体现出自身对疾病的思考。临近结尾,疾病得到有效控制,托马斯的女儿终于跟她的男朋友在家中亲昵,若是传统的好莱坞类型片会就此作结,给人以“大团圆式”的结尾。但导演并未停手,下一个镜头是屋外一辆伐木车推倒一棵树,树上的蝙蝠叼着香蕉飞远给了猪吃,猪被屠宰后接触到厨师,忙碌中的厨师被人喊出来合影,合影的对象正是开头的贝丝,字幕:“疾病爆发第1天”。这里不仅完成了整部影片叙事结构的完整闭合,在情节上也表达出导演对以“机器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批评:正是因为伐木才产生蝴蝶效应,导致疾病大爆发,最终危害人类自身。
索德伯格作为向来以独立精神著称的导演,《传染病》的拍摄只能算差强人意,以疾病为隐喻是艺术的一种传统,而反类型叙事又大多出于题材考虑,仅有的亮点是结尾的处理。除此之外,部分镜头的使用也在突破观众的视觉禁忌,如切割去世患者的头部居然给以特写,显然,这是一直应当批判的好莱坞视觉暴力的惯常操作。(张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