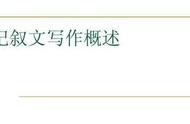多年来,周行健经常在梦里出现一个场景:月明星稀的夜晚,清风徐徐,半轮明月挂在天空,下面是一片宁静的水面,像是传说中命里的圣湖。堤岸上,一个明月般美丽的姑娘向周行健走来。他双眉紧蹙,呼吸急促,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
姑娘走过来轻轻地说:“你好!”
“你好!”周行健说着腿往后一滑,坠入湖中。
深度坠落感惊醒睡梦中的周行健,他看一看窗外,原来是列车到达一个小站停车的惯性把他从睡梦中摇醒。
多年来的梦境真实地出现。在那个荒唐的夜晚,周行健为了挽救自己不被堕落,急中生智想出一个缓兵之计。
他拨通电话,响了很久,就要绝望的时候,电话接通。
“喂——哪位?” 电话那头一个轻柔沙哑的女声。
周行健怔了一下,沙哑的少女之声,很少见,是丁香女孩吗?
“你好!请问你是林紫函吗?”
“我是。”
“噢,太好了!十分荣幸认识你!”
“你是哪位?”
“我,我叫周行健,从北京过来,你能出来一下吗?”周行健紧张得手上出汗,他豁出去了。
“你打错了吧,我不认识你!”林紫函沙哑地说。
“哦,显然你是不认识我,但我对你已是久仰美名。我是罗秉晖的朋友,很久以来他总是向我提起你,我在北京忍不住好奇,专门过来看你,看你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还是他欣赏水平太差,把东施当西施。”周行健说。
“哦,这样啊,那就满足你,见一面。明天傍晚清屏湖堤,罗秉晖知道那里。”林紫函说完挂断电话。
第二天下午5点多,太阳还高,罗秉晖带着周行健来到三天前打坐的地方。碧绿的湖面映衬着岸边的小山像洗印的胶片在银幕上一漾一漾地舒展开,将岸边的人荡来荡去。
“这不是你准备盖房子的地方吗?”周行健说。
“是的,也是我们县最美的地方,就是紫函说的清屏湖堤,实际上它是县城的水库。”罗秉晖边说边来到以往打坐的地方盘腿坐下。
周行健没有坐下,站在旁边还要说什么,见罗秉晖双眼微闭,神态自若,就把话咽回去。
说来奇怪,口口声声要见林紫函的罗秉晖今天异常平静,反而周行健像是心脏安了起搏器似的,颇不平静。他站在旁边情不自禁地想象林紫函这个在耳际被罗秉晖念叨了几千遍的女孩,今天这一刻以前周行健没有在内心关注过这个女孩,即使在罗秉晖被这个女孩折磨得死去活来垂死嚎叫的时刻,周行健也没有想过这个让罗秉晖着魔的女孩是怎样的一个女孩。
然而,直到昨晚,当周行健在慌乱中听到电话那头沙哑略显苍老的少女之声,那一刻感觉已坠入《神曲》九层地狱里经受百般拷打与折磨的他找到了魔王尾巴的空隙,在沙哑声音的引导下他逃离九层地狱,来到炼狱。
周行健说:“秉晖,你今天很奇怪,怎么你的女神要来,你还能坐在这里装高深?”
罗秉晖像没有听见他的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周行健推了他一把,说:“还装呀!”
罗秉晖扑哧笑了,说:“别闹,我不是装高深,我是紧张。你没看我全身是汗。”
罗秉晖这么一说,周行健才发现他的确满脑袋的汗,衣服后背都湿了。
周行健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她,紧张成这样。”
罗秉晖站起来,叹了口气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知怎么回事,我每次见到紫函都紧张得要命。原本攒了一肚子的话,打了几天的腹稿,到她面前就不会说了,往往结结巴巴吭吭哧哧半天说不出多少话。你知道我的口才,怎么着我也是堂堂哲学系的高才生,说起哲学那不是苏格拉底再生也是萨特转世,但到紫函面前,我就成了呆鸟一只,说不出口了。”
“怎么会这样?”周行健说。
“除了在她面前口吃,我还出汗,就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地出汗,感觉自己做了坏事似的。这种状况只有小时候我犯了错误,被我妈发现时才这样,如今却在紫函姑娘面前出现了。”罗秉晖说。
“你不会把她当成*了吧。”周行健哈哈大笑着说。
“你别说,还真有这种感觉。”罗秉晖认真地说。
“哦,有意思。”周行健说着将视线从罗秉晖身上移到湖面上。
罗秉晖的话让他从戏谑转变为沉思,林紫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把罗秉晖迷成这样,难道是神仙,难道是观音姐姐?
依偎在湖对岸山峦上的夕阳在湖面上投射出一道长长的金色光带,闪闪烁烁明明灭灭,像千万颗饱含金子...
罗秉晖与周行健在堤岸上找石子打水漂,打完一个,发出欢呼声,又打完一个,再发出欢呼声……仿佛一个个凌波飞行的石子是他们自己。石子在金色的湖面上飞行掀起的尺寸金波,在空气中带着粗粝的颗粒像高速摄影一样缓慢落入水中。这如同此时周行健的心情,罗秉晖的一席话卸去了他身上的一副重担,他知道有人比他更紧张,在看似轻松的打水漂游戏里,掩藏的是周行健渴望见到林紫函的兴奋之情,这种兴奋让周行健再一次陷入无可名状的紧张情绪里。
太阳落山,湖面的金色变成暗红,清屏堤上两人打水漂累了,坐下来休息。周行健手里攥着石子四处张望,心跳得越来越快,他是多么渴望见到林紫函。
“怎么还不来,会不会不来了?”周行健问。
“应该会来,再等等,紫函说要来就会来。”罗秉晖说。
“这么肯定?”周行健焦虑地问。
“没问题,她虽然不喜欢我,但认识以来只要答应我的事都会做到。她可不像一些女孩那样轻佻,很守信用。”罗秉晖说。
但为什么还不来呢?这个恼人的问题在周行健心里打转。他站起来走来走去,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徘徊,焦急地看着周围,期待林紫函的出现。焦虑加重了紧张感,他手心出汗,全身燥热无比,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快来!快来!快来……
“来了。”罗秉晖兴奋地说。
“是吗?”周行健问。
周行健看见远处一道亮光。
“肯定是,一看就是紫函骑摩托车的样子。”罗秉晖走到周行健前面。
接近晚上8点,天色渐暗,一辆摩托车向这边驶来,周行健的心脏怦怦直跳。虽然太阳已经落山,但西方鸡蛋清一样的澄明所折射的光还是照到了林紫函的脸上,只是这澄明之光比不上摩托车大灯的亮度。周行健睁大双眼努力想看清楚林紫函的模样,越来越近的面庞让他怦怦直跳的心咯噔了一下。
“奇怪,这样的小县城竟然也有如此灵秀的女孩!”周行健用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嘀咕。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快要下班,来了两个病人,不好推托,只好看完了才过来。”林紫函带着一个同伴,将摩托车停好,跳下来向罗秉晖道歉。
“没事没事,来了就好。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罗秉晖指着周行健对林紫函说,“这是我的朋友周行健,大诗人,从北京过来的。”又指着林紫函对周行健说,“行健,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林紫函。”
“你好,很荣幸认识你!”周行健一边问候一边下意识地将手伸过去。
林紫函有些意外,看了他一眼,也伸出手说:“你好!昨晚打电话的是你吧。欢迎你来到我们家乡!”
林紫函纤柔而微微发凉的手与周行健粗糙而黝黑发烫的手碰触的一刹那,久未握过女人手的周行健像被电击一般,全身微微颤动。这一动加重了他伸出去手的力量,用力地紧握了一把林紫函的手。
“诗人的手也这么有力,真是少见哟。”林紫函笑着说。
这句话让周行健的脸羞赧通红,他不自然地收回手,竟不知道往哪里放。
“对不起!捏痛你了。”周行健说。
或许是这一句道歉,林紫函的脸也红了。
尽管两个人的脸都红了,不妨碍林紫函日后经常拿这件事取笑周行健,说那样一副饱经沧桑的脸居然还会像个小孩似的发红,装的吧。
每次遭受取笑的周行健都会神态严肃一本正经地说:“真的!”
那确实是真的,与林紫函的第一面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女神救赎周行健,握手和四目对视的那一刻,周行健的身体血液流动加速,别说是脸红,全身都红。
站在旁边的罗秉晖看到这一幕,说:“好了好了,何必这么客气。”罗秉晖的话提醒处于紧张状态的周行健,让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有点出格。
周行健正要给自己解围,林紫函说:“哦,忘了介绍,这是我的闺蜜何盈盈,就叫她盈盈。”
罗秉晖认识何盈盈,他曾经给周行健说过,这位闺蜜与林紫函是铁杆,特别维护她,不会做任何一件对林紫函不好的事情。
周行健有意克制,不把自己对林紫函的好感表现出来。罗秉晖今晚异乎寻常的不口吃,滔滔不绝地与林紫函谈天论地,看上去也没有出汗。周行健像是着了魔,在一旁静静地偷看林紫函,仿佛看一个诱人的桃子。他心里想,莫不是在哪里见过,为什么看上去这般亲切?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在周行健心里盘问,使他忘了周围发生的一切。慢慢地,他发现林紫函不过是在敷衍罗秉晖。有一阵周行健落在后面发呆,看到前方的林紫函冲自己笑,他心里发毛,感觉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林紫函抓住。
果然,他听到罗秉晖叫他:“周行健过来,我可一直在紫函面前夸你呢。”
“就是,罗秉晖今天话特别多,说你诗写得好,我都想看看了。”林紫函笑着说。
“哪里哪里,也就是生活太苦闷,给自己解解闷罢了。如果紫函小姐喜欢,改天给你看。”周行健说。
天已大黑,一轮新月挂在西边的天空。堤坝一侧木屋旁边的电线杆上有一个瓦数很大的白炽灯将几个人照亮,远远看去几道剪影像夜里的水墨画。
这一夜特别美好,不论是对于罗秉晖、周行健,还是林紫函。罗秉晖没有料到林紫函会待那么久,两个小时,以前想都不敢想。在此之前,每次与林紫函见面,相处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对于周行健,从傍晚开始等待的紧张感贯穿了一晚上,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来电”的感觉,他不敢说对林紫函一见钟情,至少也是一往情深。从见面的第一秒起,周行健就被俘获。
对于林紫函,她说那晚的月亮很细很弯,像少女一般,被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男子俘获。
接下来几天,罗秉晖白天上课,周行健一个人在县城里转悠,不像前些天他对这个县城还有好奇,而是换了一个人,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脑海里全是林紫函。第一次见面时的疑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莫不是在哪里见过,为什么看上去这般亲切?
这隐隐而浓烈生发的爱意周行健不敢在罗秉晖面前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林紫函是罗秉晖追求两年的女孩,尽管一路猛追一路追不到,但罗秉晖对林紫函的爱是真实而浓烈的。如果他这个朋友,一个从遥远的北方长途奔徙过来被人家免费请客十余天的朋友夺人所爱,那就犯了大忌。所谓“朋友妻不可欺”,虽然罗秉晖与林紫函不是夫妻,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夫妻,但毕竟罗秉晖现在正在追求林紫函,深深地爱着林紫函。这样的思绪很快成为一场斗争,在周行健的脑海里缠斗,搞得他头昏脑涨,精疲力竭。
罗秉晖发现周行健不像刚来时那么高兴,问他怎么了。周行健说没什么,想写诗。以前在北京一起住,罗秉晖知道周行健写诗的时候比较沉闷,就没有多想。
每天空暇时,两人不再去哪,看看书,聊聊天,日子一天天过去。
星期五晚上,两人睡下很久,周行健怎么也睡不着,他也没管罗秉晖睡没睡着,忍不住隔空问了一句:“秉晖,明天周末,你想不想再把林紫函约出来?”
话音刚落,对屋罗秉晖说:“好啊,就是不知道她来不来。”
周行健又惊又喜,说:“约着看,万一来呢。”
罗秉晖说:“那你约。”
周行健说:“我约不好吧,你喜欢她的嘛,我给你们当当电灯泡就好。”
罗秉晖翻起身对周行健说:“你约吧,我约她不一定来。上次你约出来我们聊得很好,看来你是我的福星,你一来紫函与我说话的态度和神情都变了。所以你来约,就当是帮我。”
周行健有些内疚,没想到罗秉晖对他这么信任,但为了见林紫函他顾不了那么多,说:“那我试试。”
第二天是个艳阳天。周行健打电话约林紫函,她直接就答应了,主动提出来去清屏江划船。
下午3点多,罗秉晖带着周行健,林紫函带着何盈盈,一起骑摩托车在两边都是榕树和紫丁香的路上穿行二十多分钟,来到一个码头。清屏江在这里豁然开阔,有三百多米宽,水面平缓。
一条小江突然这么宽阔,周行健很好奇,在码头上看来看去。
林紫函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这条清屏江是我们县的母亲江,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都靠它。你可能觉得它怎么在这里突然变宽,那是因为几里外就是我们前几天傍晚去的水库。清屏江流了上千年,水库是解放后才修的。因为水库的阻拦,水逐渐蓄积到了这里,把两岸的树林淹没,水面就宽了。”
听林紫函说话,周行健不停点头。第二次相见,他发现林紫函的嘴不大,嘴唇很厚,肉嘟嘟的,十分性感,像半个月亮横卧,娇美动人。
“噢——这样看来清屏江真是不简单呢。每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都有这么一条江河,它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当地人,供他们饮用和洗濯。”周行健说。
“是啊,我小时候还在清屏江里游泳呢,童年的大部分记忆都在这条江里。可惜现在江水没有以前清澈,水边有很多垃圾,没法在里面游泳。”罗秉晖说。
“也不一定,如果想游还是可以的,水没有那么脏。就是水太深,看你有没有胆量去。”林紫函说。
几个人租了一条船划到江中央,在两岸都是郁郁葱葱树木的江里漂行。艳阳下,伴着江水湿漉漉的风从耳际拂过,让人感到泛舟于江上的惬意。
“如果没有污染多好,清屏江里的水就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清澈,还可以直接喝。可惜现在不能了。要我说,这个山庄都不应该开,他们在这里做餐饮和旅游,往江里倾倒垃圾,一边利用清屏江的美景赚钱,一边却又在破坏清屏江。哎,不过呢,或许我们都不该来划船,正是我们来这里消费给这些山庄带来了生意。”坐在前排的林紫函停下手中的桨说。
“对对对,污染是罪魁祸首,这些人太不负责任,只顾着赚钱,不顾清屏江的水质。”罗秉晖说。
“工业化使江村的陷落不可避免,我们今天在这里惬意地划船,若干年后可能只会成为牧歌式的回忆。”周行健忧伤地看着水面若有所思,接着说,“我喜欢这条江,它虽有些污染,但还算是一条澄澈明净的江。”
“哎哟,我们的诗人又开始抒情了。”罗秉晖戏谑道。
林紫函微微一笑,突然站起来,对着两岸高喊。
她的这一举动让小船猛烈摇晃,罗秉晖双手抓住船舷,对林紫函说:“不要这么激动,小心翻船。”
林紫函不管他,继续对着两岸高喊。这带动了周行健的情绪,也站起来跟着她高喊,边喊还边唱歌。两岸树木繁盛像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传来一阵阵回声。林紫函和周行健的回声在江面上一唱一和,像是在对唱山歌,在悠远的河道里飘扬。
小船在两人的唱和中晃来晃去,吓得罗秉晖和何盈盈死死抓住船舷。
“别闹了,船真的要翻!我们可是在江中央,水深得很!”罗秉晖大声说。
他的话引来周行健和林紫函一阵大笑,两岸树林里满是他们的笑声。在罗秉晖的强烈要求下,周行健和林紫函不再唱歌,他们坐下来看着彼此。
离开码头回县城的路上,周行健默默赋诗一首。
清屏江
弯弯的竹排
姑娘坐在前头
阿婆坐在后头
弯弯的身影,伫立
弯弯的江上
很久以前
江水淹没土地
很久以后
姑娘变成阿婆
黑黑的森林
根扎在红土地里
头枕在白云层里
江水环绕圆圆的屋顶
向太阳诉说今生的等待
弯弯的竹排
悠悠的歌声
割舍不了姑娘的企盼
改变不了阿婆的慨叹
那一江之水
不知流向何方
与以往不同,一气呵成写完这首诗,周行健没有兴奋感,而是陷入惆怅。在此以前,他的惆怅是关于诗,而这一次却是关于一个女孩。这个危险情绪的出现,让高傲的崇尚自由的从西部高原跨越一千多公里来到京城寻梦的周行健措手不及,这对他很难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周行健把这首诗用短信发给林紫函,他收到回信:
你写的?很不错。诗中的姑娘不会是我吧?
周行健回复:
是你!
他等林紫函对诗的进一步评价,却没有短信再发来。
林紫函的沉默让周行健紧张起来,心跳加速,他不停地问自己:不应该发吗?
周行健紧张地问自己的时候,他已被罗秉晖朝思暮想的女孩迷住,当手起诗落,黑字成行,周行健发现他爱上了林紫函。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但爱情降临,谁还管得了是不是好事呢。
周行健决定冒险,他趁罗秉晖上课之际,打电话给林紫函。他拿起电话拨了五六次,每次刚拨通信号还没有完全过去,随即又挂断。他不是忌讳罗秉晖,而是每次通了的时候立马意识到林紫函正在上班。她是一名实习医生,说不定正给病人听诊号脉,这样打过去耽误她工作。过了一会,周行健想她也有闲的时候,不会不停地工作,不管那么多,还是打。记不得拨了多少次,周行健逼迫自己不要挂电话,响了几声后,电话接通。
“喂——”林紫函轻轻说了一声。
“你——你好!我是周行健,我——我——”紧张的周行健不知说什么好。
“有事吗?”林紫函问。
周行健结巴了几声很快意识到不能步罗秉晖的后尘,在心爱的女孩面前结巴。
“你在解剖吗?”周行健说。
“解剖?”林紫函被问蒙了。
“对,解剖。”周行健镇定地说。
“呃——我上专业课的时候倒是解剖过几具人体。工作后就没有解剖了。怎么,你对解剖感兴趣?”林紫函问。
“感兴趣,我对解剖人更感兴趣,譬如解剖你。”周行健说。
“噢——真的吗?你打算怎么解剖?”林紫函笑着问。
“我正在研究,不过我得先知道你在哪。”周行健说。
“我在县医院上班,生殖科。”林紫函说。
这正是周行健想要知道的事情。闷在罗秉晖的房子里周行健已经快透不过气,他急需出去透气,也急需见到林紫函,哪怕不说一句话,仅仅看她一眼也好。
周行健来到大街上,午后的阳光异常强烈,照得他有点睁不开眼。人们懒懒地走着,只有周行健高昂着头颅像一位骑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县医院走去。
他向当地人打听医院的位置,按照所指的方向来到医院门口。与中国所有的医院一样,医院门诊部像菜市场,周行健淹没在里面,他有些后悔不该在午后门诊高峰期过来。不知是天太热,还是心里太紧张,不爱出汗的周行健额头上渗出许多汗珠。他在医院二楼找到了生殖科,远远站着不敢上前。他走过来走过去,徘徊又徘徊,不确定该不该出现在林紫函面前。
在酷夏的徘徊里,周行健想到东晋书法家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故事。大雪中来到戴逵家门口的王徽之徘徊良久,决定不进家门拜访戴逵,直接回去,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不如回去吧,周行健心里说。又徘徊了一会,周行健哧的一笑,王徽之和戴逵说不定是一对老基友,而我,是在追求神圣的爱情。在爱情面前怎么能退却,他决定去找林紫函。
第一个诊室里就是林紫函,她前面站着一排前来就诊的病人,林紫函半个脸在一排人里时隐时现。周行健站在最后,发现前面就诊的都是女人,他有些奇怪,难道只有女人有生殖问题。奇怪的念头很快被林紫函时隐时现的半个脸庞吸引而打消,在这样一个门诊室里,周行健近距离欣赏着朦胧美。
突然,林紫函的眼睛落到周行健身上,在半空里怔了足足有半分钟,整个房间都布满了雪花,直到一片白里响起病人的声音:“林医生,你还看病吗?”
凝固的空气才流动。
林紫函没想到周行健会来找她,看病的节奏完全乱了。一向严谨的她加快了诊断的速度,即使这样,她依然觉得时间黏稠,过得很慢。
不知过了多久,林紫函面前出现一位男病人,这是她接诊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男性病人,这个男性病人后面还排着一排女性病人,这该怎么办?
对啊,这该怎么办?同样的问题也在问周行健,他站在林紫函面前,能够呼吸到她的呼吸,能够闻到她身上淡淡的丁香味道,但不知该怎么办。身后的一排女性病人奇怪地看着他。
“你是代爱人来看病吗?”林紫函轻轻地问。
“哦——对对对,我的爱人就在附近。”多么聪明的女孩,周行健边回答心里边赞美。
“那你在旁边等一等她。”林紫函说。
“好,好的!”周行健乖乖地走到旁边。
熟悉摄影的周行健走到距离林紫函一米多远45度角的位置站在那儿,贪婪地看林紫函。
一张饱满的鹅蛋脸清新透明,一双杏眼眨来眨去,一个净瓶般的鼻子珠圆玉润,一对丰盈的嘴唇一张一翕,像半个月亮圆了又缺。
看完脸庞又看身上,可惜上身和下身都被白大褂遮挡,除了隐隐曲折的线条什么也看不到。对细节苛刻的周行健不想放过每一处,他将眼睛移到脚端,果然别有一番风味。那哪是一双脚啊,分明是两只玉兔,白嫩而粉红的脚踝,玉葱般的脚趾,被一双皮质的凉鞋半包裹着。
周行健沉浸在林紫函的美丽容颜中不能自拔,他就这样一直站着,痴痴地看着林紫函。门诊室里前来看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俩。
“看够了吗?”林紫函嗔怒地红着脸问。
“看不够,永远看不够!”周行健说。
“我给护士说了,等会再进人。这里是生殖科,都是女病人,有的需要检查。你一个男人在这里,不好给病人检查的。”林紫函说。
“哦,对不起!我这就走。只是,只是,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解剖人。”周行健说。
“看到了吗?”林紫函问。
“看到了,没想到解剖人也是这么美。”周行健说。
听到这句话,林紫函的脸又红了,轻轻说:“你来干什么?”
“看看你,一个人待着闷得慌。”周行健说。
“看够了吗?”林紫函又问。
“看不够,永远看不够!”周行健说。
“有那么好看吗?”林紫函问。
“比女神还好看。”周行健说。
“真的吗?” 林紫函说。
“真的!” 周行健说。
“好感动!——不过,这里是诊室,要给病人看病。你先回去,下班后我联系你。”林紫函说。
周行健点点头,转身往外走。
刚跨出门又转回来说:“我——”
林紫函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右手食指放在双唇前轻轻说:“先回去吧。”
周行健停了一会,转身走了。
穿过菜市场一样的门诊大厅,来到街上,斜阳照在周行健灿烂的脸上。他一路走一路笑,蹦蹦跳跳,像一匹小马,在南方小城里撒欢。他嘴角堆积着满满的美,心里荡漾着满满的爱,感觉这座城市可爱极了。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与他分享着快乐。
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个午后,也是值了。在嘈杂的诊室里,周行健像是诗人马拉美笔下的牧神从睡梦中苏醒,睡眼惺忪看到紫函仙子在橄榄树下翩翩起舞,温婉的身体在几片树叶的遮掩下若隐若现出维纳斯的美。循着德彪西为《牧神午后》谱曲的管弦乐指引,周行健离开诊室来到海边,银亮色的海浪像一幅帷幕遮蔽牧神眼前出现的梦境,紫函不见,只剩下满心欢喜。
整个下午周行健都在牧神的世界欢喜,他从县城的西边走到东边,又从东边走回西边,来回绕了县城好几圈。县城太小,装不下周行健的快乐。他不知疲倦地走,路上的人多了,那是人们下班了,他不知道;满街的饭菜味扑鼻而来,那是人们做晚饭了,他不知道;太阳落山,路灯亮起来了,那是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
不知不觉,周行健又走到医院门口,这里安静下来,不像白天一副菜市场的模样。周行健痴痴地伫立在医院门口,他在等林紫函的电话,说好下班后她要打电话给他。这么晚还没打,发生了什么事?
周行健心里犯嘀咕,他很想打电话给林紫函,又没有勇气,毕竟林紫函说她会打给他。其间,罗秉晖倒是打来几个电话,周行健没有接。今天晚上除了林紫函,他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
周行健想发短信,站在医院门口写了很多条短信,有一条写得很长,恨不得把心里话全告诉林紫函,可惜一狠心又删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勇气给林紫函发短信。
深夜11点多,执着的周行健在医院门口站了三个多小时,没有等来林紫函的电话。他想今天应该不会打了,失望地转身往回走。
夜里的小城街道孤零零的,只有周行健一个人走在影影绰绰的路灯下,像个鬼影子晃来晃去。拐到县城中学那条街,周行健看到远处有个人走过来。
“周行健吗?靠,你跑哪去了?急死人!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我正准备报警呢!”走近的罗秉晖埋怨道。
“天太热,出来走走。手机不小心关了静音,对不起!”周行健呆呆地说。
“我怎么看你像丢了魂似的,不大对劲,这几天你都不大对劲,怎么了?是不是我没招待好你?”罗秉晖说。
这句话刺到周行健的敏感神经,他的确丢了魂,他的魂被林紫函收去。只是罗秉晖不知道。看着罗秉晖,周行健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心里想,对林紫函的动心要是让罗秉晖知道了会怎样?他会恨我吗,会与我反目成仇吗?没想清楚这些之前,周行健不敢把对林紫函的动心告诉罗秉晖,他怕告诉了,他们之间就完了。
“怎么会呢,你对我这么好。待久了,对这里熟悉了,就想出来走走。”周行健说。
这句话符合罗秉晖对周行健的认知,他知道周行健会写几首诗。诗人嘛,情绪起伏很正常。他没有多想,更没有想到周行健的心思会在林紫函那里。
两个人一前一后抽着烟,罗秉晖的烟圈被周行健的脑袋砰砰地撞开,像高速摄影一样缓缓淡化成过眼云烟。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周行健脑海里徘徊,他起初觉得爱慕林紫函会对不住罗秉晖,作为朋友这样做显然不对。现在开始改变,他认为追求一个被罗秉晖单相思的林紫函是个人行为,与罗秉晖无关,因为罗秉晖和林紫函之间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他对林紫函的爱慕完全不受罗秉晖影响。这就是周行健,面对一件复杂而矛盾的事情,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往往只会想到自己,不会顾及他人。
那一夜,睡在罗秉晖对面的周行健一夜无眠,他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住在罗秉晖家里,得搬出去住,那样追求林紫函的时候心里不会愧疚。他在腹中给林紫函写了一夜短信,有好多好多话要给她说。
黎明时,只发出一条:
紫函,知道吗,第一次在清屏江堤等你时,我的心就跳得厉害,你迟迟不来,越发跳得厉害,整个人都在颤抖。见到你时,心跳得更快了,不受我控制,挣命地要跳出去。我压着,压着,压着……它却狂跳不止,一直在跳,一直不受控制。估计是患病了,跳得快要虚脱了,就要跳出身体了,就要奄奄一息了……
第二天下大雨,天地昏暗。周行健迷迷糊糊,头重脚轻,鼻黏膜粘连,鼻腔内有一堆火在燃烧,头很痛,他爬起来又睡下去。罗秉晖看他生病了,去药店给他买来感冒药。
周行健躺在床上昏睡到下午5点,饿醒了,看到手机的信息提示灯在闪烁,里面有三条短信,发信人是林紫函。
第一条,时间:上午8:00
你是袋鼠吗,跳得那么厉害?
第二条,时间:上午11:00
袋鼠生病了吗,怎么不跳了?话也不说了。口渴了吗,还是被怪兽抓走了?
第三条,时间:下午2:00
天晴了,今天傍晚6点,我们去清屏江堤看晚霞。
6点!现在都已5点多,周行健一个翻身爬起来,又跌下去,感冒没有好,跌下去的时候头旋转了好几个360度,昏沉沉的。他再次爬起来,洗漱完毕发现罗秉晖不在房间。周行健十分庆幸,不用向他作解释。他来到大街上租了一辆载人摩托车向清屏江堤驶去。
雨过天晴,碧蓝的天空点缀着几缕微云,6点正是一天光线色温最暖的时候。远远的,一个穿白裙子的身影在江堤上伫立,那是林紫函。夕阳照在她身上拉出几十米长的影子,暖风微拂,裙摆一漾一漾的像满江的碧波在林紫函身上勾勒出优美的线条。
看到周行健,林紫函微笑着说:“袋鼠生病了吗,跳得这么慢?等你很久了。”
头还隐隐作痛的周行健声音沙哑地说:“我也等你很久了,从昨天到今天。”
林紫函说:“昨天呀,我本来要联系你,结果我妈找我有事。我想反正你不走,推一天也没事,就没联系。真是对不起!”
周行健沙哑着声音说:“是吗,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周行健不得不回北京,因为他身上没钱了,他住在罗秉晖家十多天,总住着不太好,况且现如今这种状况下住着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房东给他发来短信,催他交房租,如果再拖欠不交,房东就要把他撵出去,不把房子租给他。
“明天就回!你不会是生我气了吧?”林紫函惊讶地问。
“怎么会?虽然我等你很苦,但也不会生气,最多是在夜里一个人撒撒野罢了。”周行健说着连咳了几声。
“你生病了吗?我看看,”说着林紫函伸出左手抚摸周行健的额头,“哦,好烫,发烧了,我带你去看病。”
“没事,已经吃过药。见到你病也好了三分。”周行健说。
“都烧成这样了还贫。你为什么那么想见我?”林紫函问。
“因为不见你时心慌得很,跳得厉害。”周行健说。
“见了我呢?”林紫函问。
“心更慌,跳得更厉害!”周行健说。
“你!”林紫函的脸唰地红了。
“不信吗,不信你摸。”周行健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抓住林紫函的手就往心窝里放。感冒40度的高烧加上紧张,周行健的一颗心脏咚咚直跳,带着闷声响,节奏明显比平时快了许多。
林紫函对周行健的举动没有拒绝。她的一只手放在周行健胸口,这个一夜未眠胡子拉碴的北方男人的心脏在滚烫地跳动,林紫函分不清那是感冒发热导致的异样跳动还是其他什么引起的,禁不住轻轻说:“真是跳得很快!”
周行健顺势伸出双臂将林紫函抱入怀中,滚烫的右颊紧紧贴着她的黑发。林紫函依然没有拒绝,两只手蜷缩着紧紧靠在周行健的胸口,头发被他深重的呼吸吹得一根根竖起来,像起了静电。两人正好站在横卧的夕阳中间,远远看去是一个绝美的电影镜头。
“我想我爱上你了。”周行健沉重地呼着粗气说出了见到林紫函以来他最想说的话。
或许是高烧的缘故,说出这句话时周行健竟然流出了热泪。他赶紧腾出一只手拭去,不让林紫函看到。
“我也是。你这匹北方的狼硬生生闯入了我的生活。”林紫函说。
“你是说齐秦的歌吗?”周行健说。
“你比歌更动人。”林紫函说。
在一片如梦如幻的霞光里,周行健很想落入俗套地去吻林紫函。他正要将呼吸深重一张一翕的嘴巴移过来,闻到林紫函身上淡淡的丁香味,他停下来,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重度感冒的病人嘴里的味道是很不好的,黏糊糊臭烘烘的,这样去吻丁香一样的林紫函,是对她的一种亵渎。周行健用右颊紧紧贴着林紫函的秀发,光是这秀发的味道就足够。
周行健和林紫函拥抱在一起,直到身上的金色变成红色,再变成淡淡的黑色。两人没有倦意,隔着衣服的身体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彼此心脏的跳动。两人享受着晚霞,享受着爱,享受着美。
在甜蜜的夕阳里浸润多时的周行健,完全研究透了拍摄夕阳时需要的色温,他正要为自己在爱的甜蜜里开小差的举动而自责时,有蚊子飞到他的鼻尖,他吹了口气驱赶蚊子,顺势将脸转过去,原来晚霞下的县城也很美。
唯一不足的是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挡在中间,离他们很近。周行健揉了揉眼睛,想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这让他大吃一惊,高烧全退,那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罗秉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