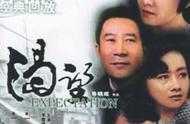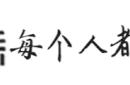从《渴望》到《人世间》看大众文化生产
很明显,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渴望》生产与走红的经过,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当代中国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的生产秘密。
众所周知,与电影一样,中国电视剧一开始不是自创的(1980年颇受欢迎的《敌营十八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电视剧),而是是外来引进的,像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的《血疑》、港台的《上海滩》等,最早把一种大众化的新兴文艺形态和“合家”荧屏观看习惯带给了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世纪初的观众。
《渴望》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寂寞和大众文化潮流中。“1990年《渴望》的热播,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收视热潮,初步显示了电视媒体巨大的传播功能和轰动效应。1991年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及稍晚时《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等的相继播出,差不多又迎来了一个‘王朔电影年’之后的‘王朔电视剧年’”[1]
笔者曾经认为中国影视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历程:“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大众化,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种别无选择和自然发展,是主流、大众、知识分子、市场化资本等的合谋和妥协,与西方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并非完全一致”[2]。《渴望》堪称中国影视大众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界碑。

《渴望》的重要策划者(这在中国影视剧生产中显然是一个新事物,这一角色的出现也是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王朔回忆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新落成的一个摄影棚促成了《渴望》的问世。因为只有每日拍摄才能维持这个摄影棚的运转而不至于亏损,所以,“要形成规模,讲究效益,必须走到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一条路上来”。
工业化的生产无疑与个性化、独创性的文化想象截然有别:“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对生产力提高的渴望改变了生产关系。一进入这个剧组我就感到了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大家上来就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到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这部戏的主题、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报……”[3]。
在这个模式之下,故事的组织就被纳入到了城市文化工业的装配过程之中:“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有一个好人,就要设置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一个住胡同的,一个住楼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默默的;这个人要是太好了,那一定要在天平另一头把所有倒霉事扣她头上,才能让她一直好下去。所有角色的特征都是预先分配好的,像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你只能直行,你只能斜着走,她必须隔一个打一个,这样才能把一盘棋下好下完,我们叫类型化,各司其职。演王亚茹的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不喜欢或不相信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合乎人情的,找导演谈,导演也许很同情她,但他也无法对这个角色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四十集戏全指着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搅了。我们搞的是一部大众文化产品也叫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有它自己的铁的规律,那是你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无从逾越的,它必须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个个走极端。在这样的作品中追究作者的艺术抱负是痴人说梦,由此判定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常常会发生误会。很多人谈到《渴望》中相对负面的王沪生一家,因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指责作者有反智倾向,其实这一角色身份的设立纯系技术问题,本来大家的意思是写一个老干部家庭,因可能更易造成误指,遭小人口诬,便放弃了这个其实更典型方便叙事的人物身份。现在好了,现在有大款阶层,所以大家一想到要在剧中给好人设立一个对立面,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这帮倒霉蛋,把人类的所有缺陷所有屎盆子都扣他们脑袋上,也没人心疼。”[4]
从王朔的回忆看,《渴望》的生产还颇具有大众文化生产的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特点。王朔等创作者对于不同于主旋律电影、主流电视剧生产模式的大众化生产方式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已经展开的中国影视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显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剧痛中,中国影视人开拓视野,实施“拿来主义”,“摸着石头过河”,逐渐探索出一种被笔者称为“大众文化化”的生产方式,这为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大发展,也为理论建设上例如工业化理论、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人世间》堪称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著名作家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的原著,奠定了这部作品扎实的人物、人物关系和细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质感,从而经由典型的故事、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呈现了宏阔的史诗性。

比之于“策划”出来的《渴望》,《人世间》的现实主义成就无疑更为巨大,《人世间》完全担当得起现实主义以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环境和真实的故事情节,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的要求。
很明显,《人世间》的史诗性不是通过大人物、重大题材表现的,而是以一种小人物、大家庭的视角去展现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和共和国近50年的变迁。
这种以平民大家庭为主体的表现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封建大家族表现传统(如《家》《春》《秋》、《雷雨》《财主的女儿们》)不一样,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大量的以“帝王之家”、“大皇族家庭”为表现主体的影视剧作品,它是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表现“小人物”,定位于“小人物”的“民生化”的作品,堪称具备“人民性”的作品。
围绕‘光字片’的人和事,这部剧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动人的细节、人性的温暖,寄托和表达了普通百姓‘过好日子’这样一种非常朴素、温情、善良的理想,这是“接地气”的,很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梦”。
《人世间》里的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性格饱满、道德良善。而且不仅作为社会大多数的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如此,作为文化知识精英如北大毕业成为高级干部的周家老大周秉义,也始终与底层民众血脉相连,为民众办实事的初心始终坚持不渝。
女性形象:郑娟与刘慧芳的不同
文学艺术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一直是艺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问题。20世纪以来,无论是启蒙、反封建、现代性还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话题、话语都与女性想象、女性想象有关。在新时期,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塑造经常引发讨论争鸣。例如谢晋导演就非常重视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成为谢晋表达思想内涵的重要渠道。吴琼花、冯晴岚、宋薇、赵秀芝、胡玉音等魅力独具的女性形象系列构成谢晋电影的重要风景线,也是阐释谢晋电影的重要途径。

“谢晋写人,最主要是写人的独特命运,他尤其擅长对女性独特命运的描写。在他的影片中,最有光彩、最富魅力的是那些有着独特命运的中国妇女的美好形象”[5]。但谢晋电影的女性形象却曾经被新锐的青年评论家反思、质疑乃至批判。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朱大可在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中曾经批评过:“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妇女在此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仅仅被用以发现和证实男人的价值并向男人出示幸福。”
当年朱大可的文章固然不免激进,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还是不妨询问,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表征或隐喻中国女性开放、现代化程度的文学艺术中的女性形象,是一种什么状况?无疑,从《渴望》到《人世间》,从刘慧芳到郑娟,无疑具有标本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