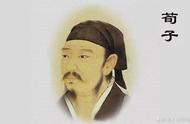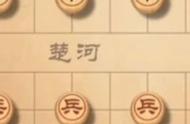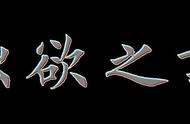梅兰芳、肖长华《女起解》
京剧角儿制的出现,是京剧班社由徽班时代过渡到京班时代的最主要标志。现有资料表明,清宣统元年(1909),著名青衣王瑶卿在北京东安市场丹桂园自挑台柱,是近代最早的旦角挑班,京剧史上真正意义的名角挑班也大概始自此时。民国以来,名角挑班则成为京剧班社最常见的组班形式,角儿制也成为京班最根本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取消角儿制成为“戏改”的主要内容之一,京班的角儿制才成为历史。角儿制的出现,对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皆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脚色制到角儿制
宋元以来的民间戏班,组织构成基本都是脚色制。戏班人数较少,七、八人至十一二人不等,一般不少于5人,否则脚色便不齐全。泉州梨园戏旧称“七子班”,一班多为7人,分工生、旦、净、公、婆、丑、末七色。明清时士大夫豢养的家班一般为十一二人,有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面(净)、二面(副净)、三面(丑)、老旦、正旦、贴旦、杂等诸色 ——所谓“江湖十二脚色”齐备。清中叶以来,乱弹大兴,戏班人数较此前有大增,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戏班都很常见,但其结构仍然多为脚色制。
在脚色制的班社中,各门脚色在戏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演员不论脚色,也不论名气,都可以在某些戏或某场戏中为主角,班中没有专跑龙套的演员。1931年《申报》曾刊登题为《水路戏班组织之神妙》的文章,说到水路班的组织云:
戏班里的组织法,一言以蔽之,曰: 能严厉实行。……他们每一只船上,必定有一个老生、一个花面、一个青衣,不能同样的角色,都睡在一只船上,因为譬如今天在甲地演戏,演到末二出的时候,就把没有戏的人,先开一只船,赶往乙地。到乙地,即使全体因着路远赶不上,那第一只船有老生、有花面、有青衣,就可以先开锣,然后守候全体到来。所以人数最多的武戏,往往在中间唱的。他是极平等的,没有跑龙套,空着的人,谁都要去跑龙套。

程砚秋、尚小云《佳期》
角儿制流行后,名角一般都有专用场面、行头,这在以脚色制为核心的班社中则是未有的。陈彦衡《旧剧丛谈》中曾专门述及名角自带场面风气的形成云:
旧剧场面皆隶班中,由班长定其差等,分剧支配,各有专司。虽头等名角,未有自带场面者。遇有喜庆堂会,甲班之角往乙班外串,即用乙班场面。甲班场面不得越俎而代,其规则然也。长庚以三庆班长资格,以章圃司鼓、桂芬操琴,为自用场面之渐,然皆隶本班,初非为一人专设。且长庚不应外串,故仍未开自带场面过班演剧之例。长庚之言曰: “大人先生喜观余剧者,尽可演三庆布。身为班长,虽演多剧,讵敢辞劳? 若余独应外串,而使全班向隅,何以对同人?”其不应外串,为顾全大众起见,义气可风,人不能强之也。自雨田、李五为鑫培专司琴、鼓,正如左辅右弼,缺一不可,一时称为双绝。后来名角遂援以为例,人人自知场面,不由班中取材,一若非此不足壮声色,而鼓与胡琴遂成名角之专用品矣!
在以脚色制为核心的班社中,不独场面是各种脚色共用的,班中的行头也是各脚共用的。梅兰芳追述到晚清苏州著名的昆班全福班时有云:
全福班的后期,沈秉泉起班最久。班子起好了,角色也邀定了,第二步论角儿制,就是到贳行头店家,租好全套衣箱,如大衣箱、二衣箱、盔箱、把子箱……考究点的共有十八只,马虎点的十二只也可以对付得过。各角很少自带私房行头,都是穿衣箱里的行头。从前昆班的行头,讲究预备得齐全,新旧倒还在其次。因为当时每一出戏的各行角色,按着他的身份在服装上分得都相当细致,哪怕一个极不重要的零碎角色,也不能随便借用他角的行头。可以说每一个穿出场的行头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定型。如果乱穿了出来,换了一点样子,台下就会很不满意地说: “这个角色扮得勿像是戏里厢格人哉!”

郝寿臣《飞虎梦》
各种脚色只有各自守住家门扮饰的规矩,共用衣箱里的行头,才能使观众明白辨别出其所属家门,所以旧时昆班讲究“宁穿破,勿穿错”,可谓至理明言。由此看来,在角儿制成为京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前,戏剧班社以脚色制为核心(如徽班、昆班、七子班等),有其合理性,用《水路戏班组织之神妙》的作者梅魂的话说甚至是“很神妙的”,那么为何角儿制能取代脚色制?
戏班中的演员天分有别,后天因缘有异,所以事实上,即使在以脚色制为组织形式的戏班中,有些演员也会因技艺较为优秀,成为班中突出的“角儿”,引人瞩目。由于宋元以来的家班受制于家班主人,民间的职业戏班则有严格的班规约束,所以班中即使有演艺突出的演员,这样的演员也很难真正成为真正的“角儿”。但清中叶以来的社会情况与此前大异,为角儿制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首先,从外因来看,城市中商业性的戏园演出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这对角儿制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戏剧演出场所主要有三类: 一是富贵人家的厅堂演出;二是乡村的庙台、草台演出;三是城市中的勾栏、戏园演出。这三种形式的演出中,唯独后者是商业性的,但这种演出自14世纪以来一度中绝,直至17世纪中叶才再度出现(当时一般称“茶楼”、“饭庄”)。乱弹戏亦在这个时期由乡村进入城市。城市中戏园林立,市民阶层开始成为戏剧的主要观赏者和评价者。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更多关注的是“戏剧”或艺术本身,看的是“门道”;市民阶层则往往对“戏剧”之外的因素也有兴趣,看的是“热闹”。因此,戏剧表现中技艺性的成分可能会较多得到关注和欣赏,演员完全可以以唱腔、武功或“绝活儿”赢得观众的赞赏,可能成为班中极其突出的“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