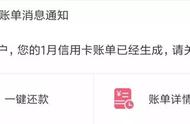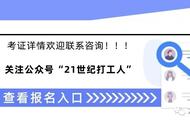网格纹鼎(夏代晚期,河南二里头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这当然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太昊帝死后,天下大乱。在大乱中“太昊鼎”也不知哪里去了。黄帝来到人世时,当时仍旧是诸侯间你打我、我打你,战事绵绵不绝。黄帝想:那不行,整天的战争最终不是苦了民众吗?于是,他一面以德喻天下,一面习用干戈,把那些“不享”的诸侯征服了,天下算是太平了。在一次封禅天地的祭祀活动中,他“获宝鼎”,也就是那久已失传的太昊鼎。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启示,太昊宝鼎就是上天赐予他天下的明证。
受到这一启示,黄帝后来就制作了三只宝鼎,以象征自己能成为天下共主,是得到天、地、人三个方面的允诺的。
到了禹平定水土成功后,禹为了仿照太昊帝和黄帝故事,也开始筹备铸鼎。怎么铸?铸多少个鼎?对他来说是个难题。一时似乎没有好的方案。后来,他正式当上天下共主有几年了,因为各地都风调雨顺,所贡的物品渐渐丰赡起来,尤其是青铜,因为格外珍贵,各地多有贡献。禹的手下施黯便请示说:“现在九州所贡之金年年积多,作何用处呢?”禹正想效仿前人功成铸鼎,又不想完全承袭他们的做法。思来想去,决定召开“九牧会议”征求意见。一听说要像太昊、黄帝那样铸神鼎,所有的人都表示拥护。铸怎样的鼎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太昊铸一只鼎象征统一,黄帝铸三只鼎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那我们就要铸九只鼎象征九州天下一统。大家都说这个意思好。“九”者,“久”也。九鼎也含有国运恒久的意思。[11]
有位州牧(州的行政长官)提出的意见也至关重要。他说:“我们铸的鼎也要把太昊帝的‘天下一统’和黄帝的‘天地人贯通’的精神融会进去,因此,这铸鼎的铜不能来自一地,应取九州产的铜,浇铸而成九鼎。”这位州牧的意见马上获得了一致的赞同。
天子禹最后总结说:“哪一州所贡之金(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该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让后世的人们懂得这江山如金属浇铸出来的一样永固。我从前治水时在那里所遇到的各种奇禽异兽、神仙魔怪等,也一一刻出。至于形象,我和伯益都有草图画出,现在一并铸在鼎上。将来鼎成之后,设法将图像拓出,昭示给九州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他们跑到山林、川泽里去劳作,遇到不好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懵里懵懂,不知利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商代晚期子龙鼎(河南辉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封禅书》)。这件夏代历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事件就产生了。
据说九鼎作为传国的重器,作为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在夏王朝的王宫里安放了许久许久。
作为传国的重器,九鼎的归属也是无常的。后来,夏桀昏聩惑乱,九鼎变成了商的宝器。再后来纣王暴虐不堪,九鼎又成了周的宝器。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时,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无功而返。
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有一则“楚子问鼎”的故事,讲的是:楚庄王时代,周王室已经十分的衰弱。楚庄王趁攻打戎人的机会,驻兵于洛水,在周王室的领地里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仪式。这时,宽厚而软弱的周定王还是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国军队。而野心勃勃的楚庄王竟大声问周王的使者道:“不知禹制作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不客气地回答:“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当年大禹是个有大德的君主,正因为有大德,远方的人们才会甘心情愿地把各种物品奉献给中央,九州的牧长也才会进贡贵重的青铜,大禹就把这些青铜铸成九鼎,让老百姓懂得何为善、何为恶,让老百姓懂得天下一统的重要性。后来夏桀不争气,鼎就流到了商,再后来又流到了周。现在,周王朝的仁德虽然在衰微,但是天命还没有改变,鼎的轻重难道是你可以随便问的吗?”在如此警告式的一席答话中,可见鼎不是一般的器物,岂能容忍楚子“问鼎”?楚庄王无言以对,只得红着脸退了下去。
写在《左传》这部史书上的王孙满的这段话,捍卫了“禹鼎”的庄严性,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说明了有仁德的人才能制作出这样的鼎来,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得到“禹鼎”这样的传世重器。王孙满的说辞中还包孕着“革故鼎新”的社会发展变迁观。《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历史的必然。夏与商、商与周之间的不断“鼎迁”,正好说明了“革故鼎新”的历史发展常规。
对于这段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如下精到的论述:“其一,《左传·宣公三年》讲‘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几句话,是直接讲青铜彝器上面的动物形的花纹的。各方的方国民众将当地特殊的物画成图像,然后铸在鼎上,正是说各地特殊的通天动物,都供王朝驱使,以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换言之,帝王不但掌握各地方国的自然资源,而且掌握各地方国的通天工具,就好像掌握着最多最有力的兵器一样,是掌有大势大力的象征。其二,《左传》里的‘贡金九牧’与《墨子》里的‘折金于山川’,正是讲到对各地自然资源里面的铜矿锡矿的掌握。‘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所以九鼎不但是通天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与技术的独占的象征。其三,九鼎的传说,自夏朝开始,亦即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始,也是十分恰当的。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12]这一精辟的论述,把“夏铸九鼎”的初衷与发展脉络说清楚了。

西周大克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泗水捞鼎”汉画像砖。出土于河南新野。此砖现藏于新野县汉画砖博物馆。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禹铸九鼎”的说法已被当代考古学发掘的成就所证实,本身就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史家认为:“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青铜的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启命人在‘昆吾铸鼎’的说法,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13]二里头遗址大量青铜器以及制作青铜器工场的发现,证明了“禹铸九鼎”的历史可能性。因为禹铸造九鼎,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还是人们常用的词汇。当然,禹所铸“九鼎”至今未见出土,仅见于史料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正像西欧的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人、又是近代历史的第一人一样,大禹也是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物。他可以说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人,同时,他又是新的阶级社会的第一人。
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抛弃一个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即将被淘汰的社会的同时,又充分地从传统社会中吮吸了多少万年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思想养料。这样,作为一个新历史时期打头阵的领军人物,他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列祖列宗的血液,音容笑貌,酷似乃祖,精神气质,一如圣贤,而他的所作所为,又是在悄无声息地埋葬一个旧世界,打造一个新世界。
他在传统社会中,是道德的楷模。帝舜时,就提倡“令民皆则禹”。“则禹”,就是以禹为准则,即以禹为榜样,让大家都学习大禹精神,这是对的。
他在新生的私有制社会中,是个勇敢的先行者。他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把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禹,他的一生业绩本身就为“何谓批判地继承”写下了最好的注脚。
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文化大家,是读懂了大禹的——虽然各人所取的视角并不相同,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他的赞誉可说是众口一词。
孔子是禹的精神膜拜者,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可以想见,孔子是带着十分激越的心情说这番话的。他赞许禹的刻苦、耐劳、大公、无私。他所说的“无间然矣”,相当于说,这样的人我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了。
而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不只倾倒于大禹的人格魅力,还直接为禹的传子制度一辩了。他的学生万章对老师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说现在不少人都以为禹之传子是一种“德衰”的表现,说明禹的品格不及前圣。面对世人的责难,孟子断然否定。他的意思很清楚,义与不义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义”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到了私有制的存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像禹那样顺乎潮流实施传子制度,相反倒是“义”的表现。孟子维护了大禹的圣人形象。
墨子则俨然以禹的继承者自命,“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墨子·法仪》)认为自己力主“兼爱”,其源盖出于“其利人多”的大禹。墨家的巨子们穿衣、吃饭、行事,全都以大禹为榜样,他们是大禹精神的最忠诚信徒。
集各家思想之大成的吕不韦,一般不轻易赞人,可是,一提及大禹时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着重赞誉了禹的礼贤下士之风,他写道:“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人也)争矣!”(《吕氏春秋·谨听》)禹那样看重“有道之士”,无怪乎他治水时总是有那么多人能帮他了。
连历来甘心于寂寞人生的庄子也出来凑热闹,盛赞禹的品格和道德精神。他赞扬禹治理洪水的伟业,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大禹能通四夷九州,把治水的范围推向天下,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此为《庄子·杂篇·天下》中所记墨子对禹的称道:禹治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而且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结果成了个走路不便的跛子,即便那样,他还是奔走在治水道上。庄子的结论是:“禹大圣也!”他对禹的总体评价是:禹是个非同寻常的“大圣”,他的作为影响了天下大势。
我们列举诸子对禹众口一词的表彰,是想破译一个千古的秘密:作为为新时代的诞生冲锋陷阵的先驱人物,他是被后世保守派人士和激进派人士都认同的人,在他的身上,熠熠闪光的是那种普世的价值观。
禹没有因为要抛弃一个旧世界而抛弃旧世界的一切。他牢牢地把握了传统的、普世的价值精神——大公精神、无私精神、利他精神、民生精神——使他真正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大圣”。既然禹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们就不会去怀疑和反对他的事业了。
大禹的这种普世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排除了在不少先驱人物身上存在的晚节不保现象。
十三年治水的辛劳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被阳光灼伤了的变得暗红色的皮肤时常发生溃烂,他的背脊是永远直不起来了,他的腿关节出了问题,走起路来永远是一瘸一瘸的,人们笑称为“禹步”。他瘦弱,但精神还好。事关民生的九州大事,禹从来不肯搁置到第二天去办。
“五岁一巡狩,禹遵之。”(《史记·封禅书》)这是禹晚年生活的写照。那时他已年过六旬,身体更加虚弱。可是,他的脑子记得很清楚,哪一年应该是他的巡视九州和大祭天地的年份,他要他的部属为他早作准备。部属感到很为难,都病成那个样子了,还出巡?他的回答响亮而明确:“五岁一巡狩,这是黄帝开始定下的规矩,不能因我而废了规矩。”这就是司马迁写《封禅书》时写上“禹遵之”一语的出典。
这次巡狩,禹特地带上了儿子启。在定九州、铸九鼎中,启都参与其事,并赢得了“夏启贤”的美名。这次巡狩也许是禹的最后一次了,不能没有启的参与。一切让启去张罗,禹只在一旁指点。他心中明白,经过这次巡狩的历练,启一定会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代君王的。
“禹行自冀州始。”(《史记·夏本纪》)九州山山水水,都是禹熟识的。投入九州的山水怀抱,使禹的精神反而好了许多。禹与儿子启一起,每天都要同民众会面,从闲聊中体察民情、民心、民风。启年富力强,上上下下跑个不停,一如禹当年一样活跃热情。他与民众的贴心,也一如父亲,这是让禹最为高兴的。
这次巡狩的重头戏是要进行一次封禅大典。“封”就是封土为台,祭上苍;“禅”就是辟土为场,祭地王。从三皇五帝以来,祭天的地方在泰山,这已经约定俗成,不可更改。而禅地可因情势而变。在封泰山之后,禹问启:“你看,禅地放在何处为妥?”启不假思索地说:“会稽是父亲治水的最后一站,又曾是会合诸侯的处所,把禅地放在会稽吧!”禹笑了,满意地说:“你说的正是我想的,就把禅地放在会稽这块风水宝地吧!”
在“禹封泰山,禅会稽”过程中,启一直是打前站的。忙完了泰山之祭,启马上奔赴会稽山。等大禹一行来到会稽山时,启已经在会稽山顶辟出了一块三丈见方的平坦的祭地,香烛等也一应俱全。禹缓缓地上得山来,神态自若,而体态虚弱。
禹在祭地的东首坐北面南,让启站立在自己的身边,九牧和各路诸侯就站立在他们的身后。司仪官宣布“禅地大典”开始,当司仪官要禹讲述祭词时,禹却把目光投射向站在自己身边的启。司仪官心领神会,邀请启口述祭词。启也不谦让,只是在讲述过程中申明是代表父亲口述祭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