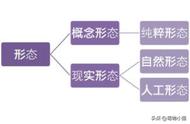而自然不是作为布景,就是通过象征而具备人的性格,使得自然被寓意化、人格化、边缘化。
旦人有万物之主的错觉,俯视一切,那么任何事物都是可塑造的,甚至是自然秩序。
在莎翁的悲剧中,景色不再是色彩绚丽的自然景色而多是荒原,这不仅是自然景色的荒原也体现了人类道德精神世界的贫瘠。

因而,文艺复兴时期机械论自然观把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性,歌颂人的巨大创造力,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又由于矫枉过正,过分地夸大人性,使得自然最终沦落成为人类生活服务的工具。
这种征服式自然观为以后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取代了希腊哲学的统治地位而一跃成为西欧的精神支柱。
但是,正如托马斯阿奎纳所说:“信仰和理性都是通向天国的道路”。
基督教神学非但没有拒斥科学,反而将科学纳入到神学的框架内,进而作为辩证自己教义的基础。

文艺复兴承上启下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神学自然观的持久存在:一方面是势力依然强大的西欧封建君主出于自己的统治需求,企图用基督教神学中众教徒对上帝的绝对信奉来告诫子民对自已要绝对忠诚。